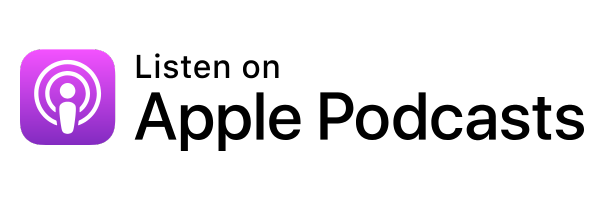今天我要讲的,是最近的一些思考。“圣经世界观与宪政主义”,也许你听起来很奇怪,宪政是时髦的概念,离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比较远。但“世界观”老掉牙了,似乎离官方意识形态比较近,我们上初中一年级,耳朵就听得不耐烦了。为什么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讲?这和我说多学科的视角有关系的。其实你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然后你对它的理解,包括对政治制度、法律,文化,包括你对个人的生命,对家庭,社会,我会说有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图景,在你头脑里。
前段时间我在法国一个短期访问,和一个记者对话,几次谈到基督徒的世界观。我说一个基督徒眼中的世界观,即一个世界的场景是如何这般的。她就说,你使用“世界观”这个词,是否说明你的思想资源里,还有一部分意识形态的遗产?你还是受共产主义传统教育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从小就听说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还听说要改造世界观。我说不是。这是一个又需要重新启蒙的东西,到底什么是世界观?共产党来的时候,他从欧洲带来的不一定全是坏的,到他要走的时代,当初他带来的一切都臭不可闻了。
所以我今天围绕“宪政主义与圣经世界观”,准备讲五个问题。
第一,人类历史上只有过两种整全的世界观
“世界观”这个词最初是康德用的,是德语的概念。后来风行在19世纪的欧洲哲学中。世界观就是你的思想中,有一个对宇宙和人生的整全的看法,一个理解的模型。就像观察地球,就有一个地球仪。世界在你心中,也有一个类似地球仪的模型。这个模型就是世界观。你所认定的人生意义,你在个人生活和政治共同体当中所有值得追求的价值,你对包括政治、国家、民族、经济、文化的看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景。这个图景就是“一个人对宇宙的总体性回应”。你对一切事物的理解,不是火花式的,也不是集锦式的,一定是整全性的。只有整全性的,才能安慰人,才可能与终极的意义相关。
换句话说,你的世界观如果是残缺的,矛盾的,不能自洽的。就意味着你的世界在本质上是虚无的。你的人生也是虚无的。你就落在深渊当中。正在落的时候,你说自己是存在主义者,落上几分钟,你连存在主义者都不是了。如果你不想用“世界观”这个在我们的传统中显得意识形态化的词语,你可以称之为“世界的图景”。 然后你才能把自己放在其中,知道自己在这幅图景当中的位置。借用我们今天很世俗的一个说法,叫做“定位”。我们会从一个市场的、或者人际关系的角度说,我要给自己一个“定位”。我的定位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身份或者个性与风格?但你把这个定位放开来看,你到底怎样在宇宙万物中给自己定位,怎样在人群中给自己定位,怎样在时间的洪流中给自己定位?
“世界的场景”,是维斯根斯特谈论世界观时使用的一个概念,海德格尔也多次评论这个概念。但当他们说“世界的场景”时,那个场景已经断裂了,价值已经不再被视为一个事实。所以他们都引向存在主义的流派。其实当韦伯虚构出一个社会科学的所谓中立性时,就已经把西方知识传统中的那个整全性的世界观打破了。这样就进入了现代社会,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找不着北的社会。在西方古典时代,信仰传统或者说价值传统,与知识传统是一个整体。韦伯终其一生都在信仰的门外徘徊,他的心必须刚硬起来,把世界摔成两半,不然就痛苦死了。可摔成两半之后,就更加痛苦。如张爱玲的《半生缘》,到了末尾说,“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然后你会看到,人类史上只有过两种整全性的世界观。一个是圣经世界观,人类的一神教传统,都程度不同地分享着这一世界观。其中以清教徒的世界观,或者叫福音派基督徒的世界观最为典型,它很好地阐释了《圣经》中对宇宙与生命的一个完整的看法。它提供了一个场景,使一切都在其中获得意义,或者说一切都在其中与真理相遇。用《箴言书》的话说,就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用《创世记》的话说,就是“各从其类”。佛家说人生的七苦谛,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但佛家给不出使一切都有意义的一个完整性的场景,于是它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的基本立场,是两个字,“放弃”。佛家和道家都没有办法产生出法治文明,因为“时间的经过”在它的场景中没有价值。所以黑格尔说,在中国,时间停止了,又或者从来没有开始过。而法治文明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时间的尊重。你怎么理解“谁主张谁举证”的普通法原则?怎么理解“两种权利相遇时,较古老者获胜”的程序正义?怎么理解法律的保守主义品质?我等会再谈这个问题。
基督教并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那样一种“宗教”,就是和物质世界无关的,和公共生活无关的一个领域当中,有那么一种所谓的“个人信仰”。它负责在人脆弱的时候安慰人,其他的事还是其他的事。不是,基督教是一种整全的世界观,一种与任何非基督教文化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连反基督的尼采也承认,基督教“是一个体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世界万物的总的看法”。在基督信仰之前,世界是破碎的;基督信仰被抛弃之后,世界也是破碎的。
清教徒的世界观是一元论的世界观,即价值世界和自然世界是同一个世界,灵魂的世界与物质的世界也是同一个世界。时间是一个舞台,是创始成终的舞台。能把价值与事实、灵魂与肉体连在一起,放在同一个舞台中的那一位,就是上帝。如果没有上帝,这两个世界就会断裂。语言和语言所指向的意义就会断裂。我所说的整全的世界观,就是一元论的世界观。而古希腊的哲学,以及中国和印度的古代哲学,都是二元论的。二元论的世界观下,你不可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图景。当然也不可能有一切事物的“各从其类”。你找不到那个位置。那个位置是“测不准”的。世界是漂浮的,所以法律的意思,要不然是成王败寇,要不然就是刻舟求剑。
在奥古斯丁那里,一元论的基督教的世界观,开始战胜了欧洲的异教文化,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及其关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画。到了宗教改革,加尔文主义第一次整全性地论述了《圣经》的启示,带给福音派基督徒最完整的世界观。基督徒们用这样一种世界观,几百年来一直抵抗着各种强盛的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和专制主义的世界观。
第二种的典型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以法国大革命为起点,以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马克思为枢纽,并得到科学主义的支持,从而在启蒙运动后一两百年内,逐渐形成了在无神论基础上的,对清教徒世界观的一次全面模仿。康德虽然提出了世界观的概念,但他的“世界”已经是一个走向二元论的世界,就是从基督教向着异教文明(古希腊文明)转向的一种世界观。尽管作为最高理性的上帝仍然在逻辑上是独一的,但上帝的主权却被切割了。所谓世界,就是人所感知的那个世界。价值世界和自然世界开始分道扬镳,一旦割裂,就再也无法合成同一个世界。只有两条路,要么你回到上帝那里去。要么继续向前,用彻底的唯物主义,把价值世界彻底干掉。那么你也可以重新得到一个一元化的世界观。就是一个被强奸了的世界,也就是共产主义。如果你什么盼望都没有了,你的世界观看起来也是统一的,佛家把世界统一在虚无当中,共产主义把世界统一在专制当中。那些既不信佛、也不入党的人呢,就活在后现代式的拼贴当中。
近代科学,正是基督教世界观的产物。科学的产生,得益于三个主要假设:第一个是宇宙(世界)是井然有序的;第二是这个有序的世界是可知的;第三是你有发现这种秩序的动机。基督教在一神论下给出了这三个回答。宇宙是被独一的真神创造的,并在他的慈爱和大能下被护理。有规律,也有目的。万事相互效力,去达成宇宙与时间的那个目的。上帝是自我启示的上帝,他给了人理性,去认识他在万物中所隐藏的知识。认识上帝,赞美上帝,就是最大的动机。近代科学是因为这个动机,而不是因为赚钱的动机,才得以诞生的。
回头看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是远鬼神的,道家说“道可道非常道”,“非常道”还研究什么呢,只需要面壁,不需要实验室。古希腊古罗马是思考哲学的,但哲学之上的世界是诸神的世界,诸神喜怒无常,连自身都受不可预测之命运的捆绑。这些宗教与哲学,都没办法支撑起这三个假设。只有一神论下的世界观,才可能提供这三个有确据的假设。结果近代科学的主要奠基人都是基督徒,甚至大都是教会的神职人员。
但科学家发现的规律越来越多之后,就逐渐骄傲了,变成了自然神论,就是我相信宇宙有一种主宰性的力量,但我不确定那是什么。于是自然或自然规律本身,便变成了神或神的临在。神的位格一旦被虚化了,随后再一变,就成了无神论下的科学主义。把科学当作真理或真理的标准,科学被意识形态化,成为了各种反基督教的世界观的依据。所以你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照刚才讲的近代科学产生的三个假设,几乎就是一个无神论版本的抄袭。基督教世界观的三个假设,就变成了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这个辩证法的某种神学色彩其实是很浓的,其实是无神论者的“天条”。这样就形成了共产主义对宇宙、世界和历史的另一套整全性的看法。
回头看自由主义和自由派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虽然是反共产主义的,但自由主义眼中的世界图景,其实还是和共产主义非常接近。“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句话几乎是一个相同的起点,是共产党及其一切世俗敌人的统一战线。“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是他们共同的目的论。只是自由主义把它换成了“自由民主一定要实现”。89年|天安门前|那些反专制、要民主的大学生,他们当时唱得最多的有两首歌,一是《国际歌》,一是《龙的传人》。从这两首歌,你就大概可以在脑海中想象和展开一幅宇宙的场景了。而这个场景和一墙之隔的中南海里面的人,其实是高度同构的。庙堂内外,他们对政治的见解虽然针锋相对,但大学生和知识精英们的世界观,他们的基本框架,其实和共产党的世界观也只有一墙之隔。世界观才是最深入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决定你的政治主张,而不是相反。
这是第一部分,我先抛出一个结论,人类史上只有过两种整全性的世界观。基督教的,和共产主义的。其余的世界观,都是二元论、多元化或拼贴式的,也就是不整全的。其实这也是中国的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结论。因为在改革开放初期,82年的中共中央19号文件中,他们也是这么说的,“在世界观上,马克思主义与任何有神论都是对立的”。
(这是十年前,2006年11月在上海“青年律师沙龙”上的讲座内容。感谢当时的邀请者张培鸿律师和组织者斯伟江律师。赞美主,今天他们都成为了我亲爱的主内弟兄。待续。)
2017-02-03 08:00
——摘自王怡的麦克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