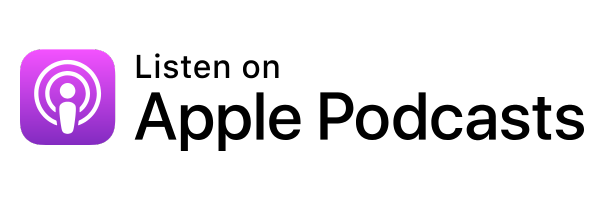当年中国留学生卢刚的校园枪杀案。我等这部梅丽尔·斯特里普与刘烨的对手戏,直等到我也成了基督徒。去年终于决定公映,又遇上韩国留学生赵承熙的校园枪击案。就一直延到现在。
8 年前,在网上读到安·柯莱瑞的家人写给卢刚父母的信,回想起来,那种震惊、隐约的盼望,及明显的羞耻,就一直存在心里。如一颗盐,一点酵,叫我的身体像一棵四川泡菜,不至于一路馊下去。
尤其是和卢刚杀人前写给姐姐的信对照,更有一种深刻的绝望,驻扎在我灵魂的洞穴里。因为显然的,你知道你自己和哪一封信更接近。
杀人当天,卢刚这样写道:
“在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大概已不在人世了。牢记:不要让美国这边敲诈钱财。我早有这个意思了,但一直忍耐到拿到博士学位。这是全家人的风光。古人云,久旱逢甘露,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人生四大目标,我都已尝过。人的欲望是没有尽头的。在美国虽然吃穿不愁,但上边有大富人,跟他们一比,我还是个穷光蛋。我对男女关系已有些腻烦了,进一步对我攻了十年之久的物理已失去兴趣。……我今天到这一步,也可以说是有父母的过错在内。……最好不要让下一辈得知我的真相,否则对他们的将来不利”。
柯莱瑞女士是爱荷华大学副校长,一位传教士的女儿,出生在中国。她没有子女,对中国学生有特别的关爱。许多人回忆说,柯莱瑞对中国学生就像对自己孩子一样。1991 年 11 月 1 日,卢刚枪杀三位教授和一位同学后,闯入柯莱瑞的办公室,朝她胸前和太阳穴连射两枪。
在病房,柯莱瑞的三个弟弟牵手祷告,决定以姐姐的遗产,为外国留学生设立一份心理关怀基金。在宣布柯莱瑞脑死亡后,三弟兄签字同意,拔去输液管。随后在亲人的遗体旁,他们写下这份致卢刚父母的信:
“……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中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因为这个周末你们一定是万分悲痛和震惊的。安相信的是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样痛苦的时刻,安一定希望我们心中充满了怜悯、饶恕和爱。我们清楚地知道,如果此刻有一个家庭正承受着比我们更大的悲痛的话,那就是你们一家。我们想让你们知道,我们愿意与你们分担这一份悲痛。这样,我们就能一起从中得到安慰和支持。安也会这样希望的”。
写这样一封信,不是你愿不愿意的问题。是你在悲伤面前无能为力,在你的怨恨面前,你是被绑架的人;在你的生命中,没有一种能力,可以在一切处境下使你被释放,得自由。当时我正努力成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我不能不承认,就算我有了言论、思想、财产、结社、罢工等一切自由;柯莱瑞的三个弟弟,仍然比我更自由。
看完电影,我写下这个题目,是耶稣复活之后,在加利利海边,对回家打渔的彼得说的,“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写完后,我头重脚轻,高烧已不能忍受,就倒头睡了。结果,这个摄氏 39.4 度的夜,是我多年来最漫长的一晚。枪杀的画面,刘烨脸上一副全世界最无辜的表情,和基督对他门徒的问话,轮番在我脑里。肉体的苦痛,灵里的软弱,家庭、教会、学校,一切的难处,一起在我里面挣扎。但奇妙的是,这个晚上,我说的不是糊话,说的竟是一篇讲章,写出来是一篇美文。我心里祈祷,说,神啊,让我明天一早还能记得吧。不然真可惜了。
结果早上醒来,仍然忘光了。我说过的话,写过的字,从来没有这个晚上被忘掉的部分,那么精彩、清澈。一个更浩瀚的世界,用心理学家的说法,浮出水面的意识,只是冰山的十分之一。就像活在地上的日子,只是刘翔这辈子跑出的第一个 110 米。
就像卢刚研究的暗物质。7 月 1 日,看见了杨佳袭警案的报道。7 月 2 日,美国的一群天文学家宣布,占宇宙总质量 98%的无法观测到的暗物质,他们已算出总重量,是 1.07×10 的 20 次方千克。
物理学到了一个地步,和“金木水火、元亨利贞”已没有本质的区别。难怪影片用“金木水火土”的五段式,来描述卢刚一生的悲剧。等了这么久,但电影让我失望极了。柯莱瑞女士被描绘为一个打太极拳的中国文化爱好者,信仰中的在世情怀,在民族文化的层面上被央视化。被卢刚枪杀的同学山林华的基督徒身份,也被小丑化。显然导演的世界,也是和卢刚的信、而非和柯莱瑞弟兄的信更接近的。于是,卢刚的那个绝望和自恋的世界,被刻画得淋漓尽致。但柯莱瑞和山林华的世界,却因太遥远而变形了。
于是,一部企图借用阴阳五行的观念,来对应和诠释一个充满暗物质的宇宙论的电影,也和卢刚本人一样,陷在自恋当中,无法目击宇宙人生的真相。
导演有意将卢刚塑造为一个对暗物质满怀探索精神的人,以天上的暗物质,比喻内心的黑暗。就如刘星(卢刚)和女侍应聊天,她说,我相信上帝,相信宇宙是被创造的。刘星说,宇宙就是我的上帝。我要发现暗物质,得到诺贝尔奖。
事实上卢刚的绝望,包含了对科学本身的绝望。这个物理学天才,最终无法理解宇宙,也无法确信生命。他给姐姐的信中写道,“物理研究是越来越失望,可说是越走越觉得走进死胡同。目前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谁也不知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人们按照不同的学校分成几大派,互相攻击对方,大为吹捧自己。无怪有人说,现代物理是自己骗自己”。
我在那个夜晚,也经历了内心的幽黯。胡言话语,直到凌晨,开始思想死亡。我想,我活着就有必须要做的事;但在宇宙的层面上,却没有任何事是必须要我去做的。我不做,上帝会兴起其他的人做。那么不如祈求上帝将我带走吧。天快亮了,我才看见一件事,使我在接下来几天的高烧中,都被这场高烧所祝福。
我常说,人生就是“五个一”工程。一位上帝、一位妻子(家庭)、一间教会、一座城市(国家),和一个职分。但我对有形的教会、城市和职分的委身,都可能被上帝改变。就如史怀哲博士的后半生,委身给了陌生的非洲人。然而地上的日子,惟独我是我妻子的丈夫,是书亚的父亲。惟独这一份在神面前的盟约,是不可分开、不可替代的。
经过黑暗的试探,我说,加给我力气吧。使我在一个不变的位置上爱神爱人。使我像柯莱瑞弟兄一样,因为爱你比这些更深,所以连那不可爱的仇敌,也能勉强去爱。然后,变得不勉强。最后,有自由的甘甜。
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刘星吞枪自杀时,一定看见了他一直看不见的暗物质。或许,他也听见了这句话,“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他却惊呼,“你是谁”?
2008-7-23
——摘自《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中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