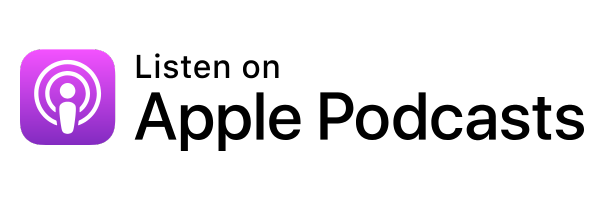有人说,莎士比亚的戏,《李尔王》最难演。就如旧约的《约伯记》。除对苦难与天意的拷问,还有一点相似,是非历史化的处境。在充满历史目的论、细陈人类家谱传承的圣经中,几乎唯有约伯记是难以判定年代的。不但如此,也唯有约伯记,将天上的故事,就是撒旦在上帝面前对义人的指控,与地上的情节直接挂钩。
《李尔王》也一样。古英文中的“莱尔王”传说,是放在基督教世界中的。莱尔王称赞两个在嘴唇上结出谄媚果子的女儿,是“基督国度里最可爱的基路伯(天使)”。莎士比亚却偏把这一英伦传说,搬回了异教世界。萧索的荒野,一如雅典郊外的阿顿森林。在对希腊诸神和女神的呼告中,人性的挣扎,越发显得壮观。这与《哈姆雷特》不同,是《李尔王》最惊心动魄之处。让人在希腊悲剧与哥特式悲剧之间,看到灵魂的颠沛流离。比起哈姆雷特圣徒式的沉思,还是李尔王在暴风雨之夜的癫狂与叫喊,比较接近我们的时代。
也更接近发出旷古之问的屈原。宇宙论上的“明明暗暗,惟时何为?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创造论上的“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目的论上的“遂古之初,谁传道之”?历史论上的“鲧何所营?禹何所成”?或“周幽谁诛?焉得夫褒姒?齐桓九会,卒然身杀”。最后指向终极的道德论,“天命反侧,何罚何佑”?
令人戚戚的是,屈原之后,华夏几乎再没出过这般撕心裂肺的天问。这使屈原的故事,像中国史上一段约伯记的残篇。即便年年端午,也不过是留恋他水平方向上的激情,却舍掉了他垂直方向上的尖锐。
我大概看过三个版本的李尔王,包括黑泽明的《乱》。就算是他,在东方的人性视野中,也有拉平超验之维,回到家国伦理层面的倾向。但这部电视电影,出自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舞台化的场景,道地的台词,原汁原味,痛快过瘾。
据说好莱坞也在筹拍《李尔王》,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也让我期待。只是那种天上地上的张力,从人嘴里吐出的话中,藏着一个绝望与怜悯交替出现的宇宙。
这样的灵魂中的恢弘,对好莱坞来说,可能过于奢侈了。
最近也看俄罗斯送选奥斯卡的《蒙古王》,成吉思汗的电影,也有少说三五个版本了。耳熟能详的情节,丧父、失母,被掳、为奴,最后兄弟反目,成就霸业。就如李尔王的公爵葛洛斯特的预言,“亲人互相疏远,朋友变为陌路,弟兄化为仇敌,城里有暴动,国家发生内乱,宫廷里潜藏着阴谋”。或者耶稣在《马太福音》中说得更怵目,“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
《李尔王》正是这一末后境况中的哀歌。如 C·S·路易斯评莎翁的十四行诗,说他的文字,永远交替着慰藉的爱和绝望的爱。《蒙古王》却相反,铁木真的血气、苦毒和仇恨,在对家族利益的捍卫中,被不断地神圣化。影片也描述了一个异教时代。先知一般的老僧,祈求被囚的铁木真,将来灭汉时不要毁没寺庙。铁木真的一生,也数次在草原的狼图腾前跪下。不是与神同在,而是与狼共舞。
可怜对铁木真灵魂的刻画,实不及李尔王的百分之一。我们似乎永远走不进君王的心灵世界。无论电影或文字,东方的君王,依然被描述为某种意义上的超人。葛洛斯特的儿子爱德伽,在逃亡途中,唾面自干,在污泥与猪食中滚爬。一位沦为乞丐的王子,成为伟大力量的象征,而不是复仇的积累。李尔王见到面目凌乱的爱德伽时,说,“他使我想起了人不过等于一条虫”。就如约伯包裹在身体的苦痛中,也这样叫喊,“对虫说,你们是我的母亲姐妹”。
在莎翁笔下,君王并不是另一种人,君王象征着人人与生俱来的尊贵身份。丢弃这身份后,君王也不过是可怜的汤姆。这就是莎翁的历史剧,与我们迄今为止的古装戏,一个尚未被逾越的鸿沟。
当考狄莉娅说,父王,我按着自己的分爱你,一分不多,一分不少。我不能像姐姐们,明明结了婚,却说父亲是自己唯一和至高的爱。李尔王被激怒了。在圣经的婚姻观中,水平方向上的夫妻,永远高于垂直方向上的母子。因为有一位上帝,在一切关系中,都站在至高处。这也是多少中国家庭的困境所在。垂直关系的显赫,代表着家族与祖先的崇拜。李尔王被激怒,是因为他不但想做女儿的父亲,还想做女儿的上帝。
考狄莉娅重逢癫狂后复苏的父亲,她跪下来,请父亲为自己祝福。李尔王也跪下来,求女儿饶恕。这是剧中最美善的一刻。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怜悯永远是苦难遮不住的美德。爱永远被描述为付出,而非斩获。但考狄莉娅与父亲在得胜一刻双双死去,还是令人猝不及防。有人说,这正是人类经历中两大高峰的汇合,一是失去的都已找回,悲哀已被擦去;二是肉身的失去即死亡的突如其来。
我在北川中学的废墟,捡拾了孩子们最后一课的笔记,从岁首到年终,人说,你们基督徒怎么解释灾难呢。我说,在这个看得见的世界,灾难是无法解释的。莎翁在《李尔王》中没有解释,爱德伽抱着父亲叫喊,我们的罪孽是上天惩罚我们的工具。李尔王的二女婿为妻子的罪忧伤哀叹,甚至说,赶快降一次灾吧,否则必有更大的灾祸接踵而来。莎翁描述的,是一个不可解释的世界所承受的沉重疲乏。是的,我们的思想是我们的,但结果却不是我们的。
《约伯记》也没有给出解释,在似乎无辜罹难的三次试探中,无论质疑上帝的公义,还是最后在尘土和灰烬中懊悔,约伯都永远不知道第 1 章和第 2 章的存在。但所谓信仰,就是在超乎因果解释之上的神秘性中,去信赖整个宇宙的道德性。
又回到那两句经文。《诗篇》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这话语叫人温暖。但《约伯记》说,人算什么,你竟试炼他?这叫人发现,活着真是尖锐无比。在《鲁宾逊漂流记》中,就算鲁宾逊远离了世界,最打动人的还是这句台词,“从罪中被拯救出来,远比从苦难中被拯救出来更重要”。
今天清晨,友人发来短信,说诞下一子,七斤三两;取名宁录,这是圣经中一切后世英雄之父。李尔王说,我们都是哭着来到这世界的。既来之,则安之。在约伯的天平上,一边是我们的灵魂,一边是我们的苦难;一边是上帝的公义,一边是世间的英雄。活着,或是披上皇帝的新衣,或是双手握得满满的。
李尔王之死,是一切悲壮感之死。英雄死了,才有圣徒。骄傲死了,才有恩典。但愿宁录这孩子,一生有温柔的怜悯。那造他又救他的,以爱为旗,在他以上。
2008-11-14
——摘自《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中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