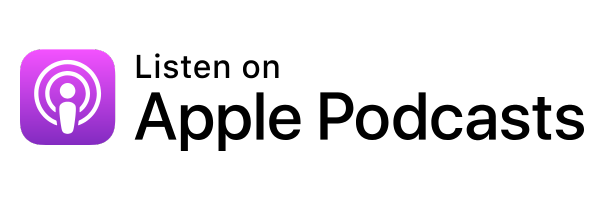近年来,知识界开始关注宗教在中国的复兴,尤其是基督教的传播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
因为各种本土宗教与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与社会形态具有较强的同构性,而基督教无论在其独一神论和救赎论的教义层面,还是教会生活的形态层面,对中国社会的肌理而言,都是一种异质性的文化。并与西方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政治与社会、文化形态具有较强的同构性。这也是基督教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扎根与扩散,长期被当政者诠释为一种“渗透”的原因。如果对“渗透”一语不作简单的意识形态化解读,“渗透”的确是一个很准确的描述。鸦片战争以来,西方文明的各要素,大多是以冲击、颠覆、对抗、争战的方式影响中国的。无论赛先生还是德先生,都以上街游行的方式登台亮相。几乎只有基督教,是以“渗透”的方式,在中国社会文化的肌理中一路沉淀下来。一个默默无闻的传教士,可能在一个极其偏僻的村庄里,以他数十年的传道与服务,改变了当地民众的话语方式、思维习惯、交往方式、灵魂信念,乃至寒暄问安的用语或写春联的造句。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共同体的范式。这种范式对于后极权时代的中国而言,几乎是全新、异质而充满想象力的。相当于在一个旧的社会中,渗透扩展出了一个新的亚社会。以哈耶克的自发扩展秩序来论,普世的人类自由在近现代中国的落实,几乎只有基督教,是一个典型的自发演进秩序的例子。
虽然早期的传教士们,也曾借助不平等条约中传教条款的保护。以至于在政治和文化层面,都酿成过剧烈的教案冲突。但在 1951 年,中共赶走全部外国传教士后,基督教以一种民间的、草根的、边缘的承受苦难的方式,在恶劣的政治压迫下,形成了一个蔚为大观的、中国得不能再中国的信仰共同体。新教徒从 1949年的约 80 万人,竟然在历次政治迫害下增长到 80 年代初的 800 万人,30 年后更增加到可能有 7、8 千万人之多。增长近一百倍。在中国 160 年的西方化历史上,这是第一个经受了历史动荡之考验的、彻头彻尾来自西方的、生生不息的自发演进秩序。1978 年后市场经济的逐步成形,则是中国社会的第二个西方化的自发演进秩序。第三个自发演进秩序,即政治层面的自由民主体制,则还没有形成。
很有意思的是,在迄今为止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饥渴慕义中,这个顺序刚好是反的。甲午海战后,维新派、立宪派、革命派,第一位关注的都是民主与政体,第二位是经济,宗教甚至排不上第三位。但这三个自发演进秩序在中国社会层面的落实,却出人意外地颠倒了过来。第一个成形的,是信仰共同体;第二个成形的,是经济共同体;第三个才是前面的政治共同体。
前两个共同体的成形,都与强大政治力量的介入相关。但介入的方式刚好相反。一个是打压,一个是推动。唯有当基督教这一信仰共同体的内在生命力,超过了它所遭遇的政治高压的残酷性时,基督教自发演进秩序的形成,才是可能的。从这个角度看,数千万基督教信仰群体在 1949 年后的形成,是一个社会学上很难解释的奇迹。尤其是考虑到几乎任何一种本土的自发秩序,每一个根基厚实的信仰或知识共同体,都无一例外地在 1949 年后的中共独裁政治中遭受了毁灭性的瓦解,至今没有真正恢复元气。而基督教这一异质文化在相同的政治磨难中,反倒在中国社会培育出了元气。几乎没有一种实证理论,可以逻辑周延地同时解释这一相反的社会演进。
这三种自发演进秩序的顺序,和 1949 年后中共镇压和瓦解民间社会的顺序,也是一致的。第一场“文革”从 1951 年开始,残酷镇压一贯道等“会道门”,驱赶外国传教士;1953 年到 1956 年,以软硬两手镇压基督教、天主教信仰群体。第二场“文革”以 1956 年为中心,镇压的是资本家群体。第三场文革从 1957 年拉开序幕,到 1966 年进入高潮,镇压党内当权派和同情自由民主的党外启蒙知识群体。
为什么中共的镇压逻辑,比当时乃至今天的多数自由知识分子,都更准确地吻合这一顺序,把看起来在政治上最重要“敌人”排到最后去对付呢。或者反过来说,自由派知识分子一贯自视甚高,认为自己要么是一字并肩王,要么是中共的头号敌人。结果中共第一个对付的,却是基督宗教(在本文中泛指基督教和天主教)。显然在中共看来,它与基督徒这一共同体的异质性,要远远大于它与右派们的异质性。
这一命题,正是理解中共政权之宪政转型的一个关键,也是重新理解宗教自由之于未来宪政中国之核心价值的关键。否则,今天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宪政民主带着某种制度崇拜之嫌的理解方式,和潜意识里的排序(政治第一、经济第二、信仰第三),仍将在未来可能留下重蹈历史覆辙的危险。
这一系列评论,希望从宗教自由的角度,重新理解中共之意识形态统治,并以“政教关系”为核心,论述宪政转型的实质和当代中国政教关系的事实与趋势。从顾准开始,自由知识分子开始隐约认识到共产主义的宗教性。“意识形态政治”,或“极权主义”,是一种过于启蒙式的话语方式。有学者提出“人民宗教”的概念,倒是对中共意识形态之宗教性的准确描述。
所谓宗教,是一整套具有宇宙论、世界观、以及对关乎人的根本问题与终极出路的信念系统。当这一系统的解答方式标榜某种终极性,其信念不建立在实证之上,并在人群中形成一种以此为指导的群体生活方式——包括“教义”的形成、“祭司”的群体、程度不一的团体生活、因此形成的经济联结等,我就称之为宗教。
以此,我将中国社会之宗教共同体,区分为四种:
1、启示宗教,相信启示的和独一的上帝,建立在旧约或新旧约圣经之上的信仰群体(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
2、民间宗教,在本质上的不可知和神秘主义的认知中,持守源远流长的泛神或多神信念,(佛教、道教,马祖、关公崇拜等);
3、新兴宗教,这是多与民间宗教有关,又受到某些现代、后现代哲学思想影响的,晚近历史中出现的信念系统(新纪元运动、气功运动、瑜伽等);
4、人民宗教,即以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为内核,借助国家权力建立的一整套涉及教育、就业、参政、立法、司法、宣传、出版、仪式,在各方面影响和塑造社会群体生活方式的类宗教模式。
儒家(尽管有学者标榜为儒教)在当代中国仍不构成一种宗教,这不但是从“教义”上审视,其对人的根本问题与出路的回答,不具有较明确的终极性。更重要的是,儒家对群体生活方式的宗教性影响,已基本上被瓦解。在今天的中国社会,不存在一个信仰共同体,或信仰影响下的群体生活范式,可以称之为儒教。因此新儒家只是当今的一种思潮而已。但随着祭孔等仪式在国家扶助下的建立,和儒家学堂的发展,也不排除儒家在未来与民间宗教的因素结合,形成介于人民宗教与民间宗教之间的另一种雏形的可能性。
中国经历 160 年来的积累、嬗变与反复,其最终的转型与立序,从种种迹象观察,极可能发生在未来二三十年内。这一转型包含三个层面,一是政体即制度层面上的民主转型。二是宪法权利尤其是集会、结社、新闻、出版等政治自由的复苏,及宗教信仰自由的落实,而带来民间社会结构、伦理道德、生活范式之转型。三是文化的转型,新的政统,其正当性、持续性及其生命力,都呼唤和依靠新的“道统”的形成。当代的自由主义等思潮主要是一种政治学说,宪政中国的文化新道统中,不能想象没有宗教信仰在超验的终极关怀与经验的群体生活样式这两方面的塑造力。
以四种宗教信仰的范式,来看未来的中国转型之政体与文化层面。均可解读为人民宗教与公民宗教之争。中国的民间宗教与新兴宗教,基本上是在人民宗教的范式之下被统摄(法轮功除外)。很多同情、亲近甚至认信基督教的知识分子中,对于基督教群体在第一个制度转型层面上的现实政治影响,抱有某种想象和期待。就如耶稣的时代,以色列的追随者对耶稣会带来政治性复兴的期待一样。
这些期待有些被夸大了,有些因为不了解基督信仰,因而与中共一样,基本上以唯物主义者的方式,将宗教处理为一个“政治”议题。
基督徒社会作为当代的一种自发演进秩序,其对社会转型的影响主要将在两个方面,一是基督信仰的超越性,对国家主义和一党独裁这一本质上的偶像崇拜的政治体制,在政治哲学和国家学说层面的冲击力。二是基督徒群体的生活方式,将深刻影响一个正在衰败中的、缺乏信任与活力的公共文化、道德生活、家庭价值与人际交往模式。因此基督教对中国宪政转型的影响,主要将不是政治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和文化性的。
但那种认为宗教全然与政治无关的、看似小心翼翼的论调,也对圣经和社会两方面都显得无知。不必讳言基督教对未来宪政中国之政治性的影响。就如耶稣来,不是为着颠覆(以武力方式)一个殖民的政治体制;但耶稣的信念和全部教导加起来,却对人心与国家,都必然构成一种真实的颠覆力(以非暴力的、怜悯大于指责的、及以个体灵魂为关注中心的方式)。若以中共操控下的司法标准为参照系,并考察当代既往政治犯的案例,那位以前所未有的锋利言辞,指责以色列的公会、祭司、法利塞人和一切假冒伪善的权势人物的耶稣,他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放在 2008 年的共产中国,依然是成立无疑的。这一点,正是渴望忠实于全部圣经教导的家庭教会,在人民宗教与一党独裁的中国,依然难以获得宗教自由的原因之一。
但基督教的政治性影响,基于正统的基督信仰要义,却不是“解放神学”或“社会福音”式的。而必然是以“灵魂渗透”的方式,或说自发演进的方式,而不是抗争的方式和顶替的方式。不过,越是在缺乏宗教自由的地方,越是在宗教群体的社会空间趋向地下化的局面下,教会对纯正信仰的持守,越是可能陷入试探、误区和偏差。换言之,缺乏宗教自由的政治环境,正是培育邪教、和引诱宗教群体走上弯路的温床。相反,唯有当宗教信仰自由在政体上得以确立时,才能防止宗教以错误的方式影响政治。
换言之,一个独裁政权如果打定主意一百年不变的话,基督教的确就是它最大的敌人。但如果它不排斥变化,只希望这变化是一个温和的、谅解的、渐进的、甚至是自身有安全保障并得到谅解的过程,那么基督教就是它最好的朋友。
在当代中国,基督宗教的传播对中国的政体转型,可能具有三方面的较大影响:
1、重构政教关系的压力。中国的其他宗教与知识群体,从未真正对国家不能干预人的灵魂、不能审判和强制人的精神世界这一点,也就是对国家权力最根本上的一种限制,构成过最严肃、尖锐和持久的挑战。几乎只有当基督宗教这一自发演进秩序在中国社会形成后,这个议题才在中国成为一个优先性的冲突。新教的家庭教会和天主教的地下教会,在数十年的政治迫害中,甘愿付出生命代价去坚持的,是在中国以往的文化和历史中,从来不曾排在比较靠前的一个议题。那就是政教分立,国家权力不能及于一个人的内心。换言之,因为对上帝的信仰,基督徒在世俗政治的层面,必然成为极权体制的天生反对者。因为他们拒绝国家的主权是至高的,拒绝国家权力可以掌管灵魂的事务。尽管他们在行为上强调顺服,但在内心,他们比中国社会的任何其他人群,都更加是不妥协的“不从国教者”。如果看到中共政体的本质是一种现代的“政教合一”。那么基督教在中国 50年来的存在,实在构成了政治意义上的自由秩序在中国生长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部分。在以后,随着教会与政府这一长达半世纪的地下化的尖锐冲突,开始呈现开明、温和的趋势以及进入对主流社会有更公开影响力的阶段。这一“不从国教者”的自由秩序,将对国家学说构成更明显的压力与挑战。
2、数千万基督徒社区的形成,表明基督教在中国,不是一个所谓个人性的信仰问题,而是一个丰富的、类型化的和新的群体生活方式。这一庞大人群以及群体生活,事实上构成了民间社会中最大的结社,最大的 NGO,和最大的亚社会。在这一群体从“非法化”走向合法化的过程中,将涉及的也不只是单纯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议题。而对诸多宪法权利的落实,和公民社会的形成,都具有议题拉动与先行的影响力:
A、结社自由。教会的合法登记不可能单独获得,必然与整个社会的结社自由密不可分;
B、出版自由。教会系统的庞大印刷需求,必然与整个社会的出版自由密不可分;
C、集会自由。教会的传教与布道的聚会,必然与整个社会的集会自由密不可分;
D、言论自由。福音的传播与宣讲,必然与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密不可分;
E、教育自由。教会学校与家庭宗教教育的发展,必然与整个社会在教育上的去国有化和去意识形态化密不可分;
3、在良心自由与外在顺服之间,在内心信仰与教会生活之间,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具有一种在保守、顺服与独立、自主之间的张力,在政治上显然会更多地倾向保守,和倾向对法治的尊重。因此成熟的教会对未来中国民主化的最大贡献,就是提供一大批经过了教会生活操练的、具有成熟品格的选民。反之,不成熟的教会则提供不成熟的选民。
这三类影响无疑都是政治性的,但与一个狭义和具体的政治概念,即关乎公共权力的分配运作过程,并没有太直接的关联。
基督教对未来社会与文化转型的影响,则可能是更加丰富的,更加具有道德性,以及在变革与保守之间保持张力。事实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道德层面,和文化层面,基督徒都可能构成未来中国最重要的保守主义力量。
从法治的层面说,当代中国最严重的对生命权利的体制性侵犯,集中在三个方面:
1、计划生育制度;
2、劳动教养制度;
3、死刑制度;
基督徒的信仰,在上述议题的变革上,显然具有比其他维权人群更尖锐、更内在的驱动力。那就是重新带回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尤其是计生问题,触及到基督徒对人的生命观念,与无神论群体最大的迥异之处。基督徒群体必将成为在未来推动废除计划生育的主力。就像基督徒曾经在英国和美国,成为废奴运动的主力一样。
基督徒与世俗社会的诸多文化冲突,也将随着教会的公开化,而日益成为影响社会议题与文化品格的场域,仅以婚姻家庭的层面为例:
1、对婚前同居、婚外恋和一切婚外性行为的反对态度;
2、以横向的夫妻关系为核心、而非以垂直的父母关系为核心的家庭观念的冲击力;
3、对同性恋等议题的保守立场;
4、教会婚礼、婚前与婚姻辅导、心理辅导、对离婚的劝诫等仪式与观念系统,几乎是当代中国唯一可能影响衰败中的家庭婚姻价值的、有生命力的生活范式;
在更广泛的社会领域,基督教的群体生活范式,亦将对诸多议题形成道德性和制度性的影响与冲击:
1、基督徒的什一奉献和慈善捐助,以及全时间奉献的牧师、传道人群体,对社会慈善、与公益事业的复兴,如对济贫、救灾、对孤儿、乞丐、艾滋病人及各种弱势群体的关怀的影响。
2、基督徒、牧师和传道人群体及各种志愿者的“自愿性贫穷”,即普遍地主动选择一种略低于自身有能力获得的物质生活水准的生活方式,及这种选择所蕴含的道德性活力,对当代中国社会的财富观与价值观的冲击。
3、教会在圣经原则下的治理,包括圣职人员的选立,其对仆人式领袖和服侍精神的强调。对彼此服侍与顺服的操练,中国教会若在这方面日益成熟,将对“民主”不是作为一种狭义的政治制度,而是作为一种公民社会的彼此相爱、彼此尊重的品格的养成,及对民间机构、公司乃至政府机构的治理,都可能构成巨大而独特的影响。
4、对妇女和儿童权益,及更广泛的宪法平等权议题的认同和推动。
5、对普遍的腐败、偷漏税等具有道德性的法律议题的影响。
6、教会的社区化、及牧区和教区的逐步出现,对民间社会的自治及社区共同体的模式具有的影响力。
总的来说,基督教在某种意义上的尖锐性,以及基督徒所言“光和盐”的作用,效法“好撒玛利亚人”的道德实践,以及饶恕、感恩和尊重平等等品格,在中国的政体、社会与文化转型过程中,将促使基督徒群体构成一种既有变革性,又有保守性的温和的社会力量。考虑到变革与保守、冲突与宽恕的平衡,可能正是影响中国未来转型之效果的、最稀缺的品质。基督教群体在中国的实践,其以宗教信仰自由为直接诉求的,对社会、文化和政治议题的全方位影响,并不像一些知识分子所期待的、或如政府所顾虑的那样,会对狭义上的政治变革构成直接的推动。但却有可能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发挥出人意外的、更重要甚至更关键的作用。
2008-11-15 写于红照壁。
——摘自 灵魂深处闹自由:《与神亲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