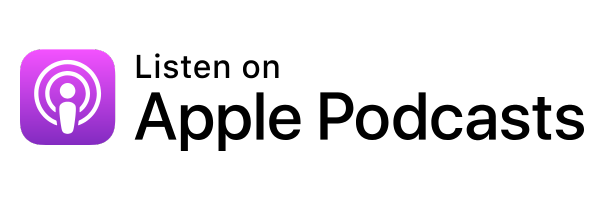从《以斯拉记》到《尼希米记》,被掳的以色列人有三波归回运动。每一次都得到了世俗情势的配合,和君王的首肯。每次都指向一个复兴与重建的主题,大卫王的子孙所罗巴伯领着民众修建了圣殿;大祭司亚伦和撒督的后代以斯拉,恢复讲解神的律法;而后,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圣殿是生命开始、事奉出发的地方。如果将1949到1979这30年,看作中国教会在逼迫中持守祭坛、养成生命根基的时代。将1979到1989、1999,再到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看作一个“在辖制之中稍稍复兴”的30年。那么一年过后,我们看见512地震无论对中国教会来说,还是对世俗政权而言,似乎都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对教会来说,浮出水面,参与社会,成为一个规模化的公共事件。家庭教会在参与灾区重建的过程中,整体上已无法隐藏,亦不可隐藏。在2008年5、6月份,据本地教会估算,来川的海内外基督徒志愿者约10万到20万人,约占志愿者的10%-20%。但到2009年春节前,据参加基督徒灾区事工联席会的灾区同工们估算,春节期间仍留在四川的志愿者中,基督徒比例已超过了90%。大地震引发的这场社会参与浪潮,除规模化和公开性之后,开始凸显第三个特点,即持续性。对政府来说,2008年-2009年的各种情势,从国力鼎盛到危机四伏,也已接近社会转型的晚期。而512之后,灾后重建和基督徒,在政府和公众眼里,也成了两个联系紧密的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2008年政教关系的变迁,和一些跌宕起伏的局势,包括家庭教会的合法性开始成为公共议题;都与基督徒在灾后重建中突出的身份彰显与信仰实践,有较大关系。
因此这一年的灾区事工,与如加州的华人基督徒积极投身于反对8号提案的运动,在异象的负担上有所不同。512已成为下一个30年的转折点。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开始进入新的世代。从旧约启示的应用上说,从圣殿到城墙,就是从建造教会,到祝福社会。从内心信仰到宗教实践。从社会学的视野说,这一年的意义,就是教会从一个边缘的、受压迫的奴仆地位,开始向着一个主流社会的位份转变。基督徒群体要开始从一个完整的信仰出发,建立起一整套公开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及行为与交往模式,从而完成从秘密团体到“亚社会”的形成。所谓“城墙”,在今日,并不是指将教会与社会分开的四面墙,而是能将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范式,与世俗的生活范式及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一个公开化的“亚社会”。这是对信徒的生活、家庭和信仰之圣洁与独特性的保护,也是从“亚社会”影响“全社会”的必经之路。
参与灾后重建,对教会来说,最重要的是因此促进了教会的社会化过程。笔者明显地看到,无论是在属灵的领导力、金钱的奉献和各类世俗资源的运用上,这一轮社会参与都呈现出四个特点,
- 以家庭教会为重心;
- 以家庭教会中新兴的城市教会为重心;
- 以依托家庭教会背景的、非教会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机构、团队为重心;
- 以非直接宣教的社会事工或福音预工为中心;
这几个特征,很大程度上可折射出中国教会的走向。反过来说,第一,“三自”系统尽管在教会的公开性和各类资源的集中上,都有家庭教会所没有的优势,但三自系统下的堂点和信徒并没有成为灾后参与的主要力量。这表明城墙的事工必然是圣殿建造和真道扎根的延伸。由政治格局所扶持的“公开性”,并不与“社会化”的程度成正比。第二,以河南教会为主的团队型系统和温州教会,是中国家庭教会前30年的主体力量之一。但有意思的是,她们尽管在灾区有积极的参与,但也不是灾区事工的主导力量。这表明金字塔式的、家族式的及不成熟的主教制(带领人)的大型教会治理系统,与中国改革30年来所形成的多元化的民间社会及其精神资源,不能完全配合,要在一个“开放社会”中担当属灵的职分,可能会有较大的困难。第三,在神学上持守基要主义、分离主义或小群主义的,以及受灵恩运动影响的教会系统,也不是这一轮基督徒社会参与的主流。
灾区事工其实是一面镜子,也是上帝建造中国教会的一个管道。观察“512”后的救助与重建工作,笔者看到家庭教会正处于一个大时代的开端,和一次充满嬗变、阵痛、试探与祝福的大转型。由此将带来对家庭教会的神学立场、属灵观和教会建造的巨大挑战。教会之于世俗社会的公共意义也将因此发生改观。
这一年,有无数信徒甘心委身灾区,使主基督耶稣在他们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但在群体性的同工上,灾区事工中出现的问题、争战、冲突;如传福音的方式及其与灾区救助的关系,对灾难的理解,及教会、机构、团队与灾区、社会和政府的关系,都可能混乱多于次序,分离多于同工。笔者看见许多团队因着在真理、异象、属灵传统、工作方式、金钱管理、权柄与次序上的冲突,陆续走向解散、分裂。尽管这些弟兄姊妹在经历挫败、委屈之后,大多仍在灾区坚持服侍。
这样大规模的灾区事工,其实是对一个跨教会的基督徒“亚社会”的考验和彩排。一年后看彩排结果,笔者的结论是,中国虽有可能高达8、9千万的基督徒,但我们还远远没有形成一个“亚社会”。若我们可夸口的,只是个人见证的汇集,而非一个因着真理、而在爱中联结的“基督徒社会”的群体性见证,能如城墙一般,将我们与其他亚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及交往方式区别开来。我们这一年,往后看,有美好的见证求主记念;朝前看的话,仍旧是失败的。如同组织灾区事工联席会的“香柏”领导力机构,所看见的“筑山上之城”的异象;既是对这一转型的属灵的描述,其实也是对当前困境与挑战的自白。
基督徒的NGO元年
城市教会从人数上来讲,远不如乡村教会。但她们所处的社会地位、资讯与资源,及各方面的介入能力,包括在神学立场和属灵观上受基要主义与分离主义的影响较小,而受归正信仰、基督徒的文化使命观、及洛桑会议对基督徒社会参与的立场的影响较大。当她们成为灾区参与的主体时,就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即机构的出现。在乡村教会阶段,不太可能有机构产生。教会承担了有限的社会事工,甚至也从事营利性事工。基督徒机构(NGO)的出现,则是教会社会化的结果。2008年5-8月,笔者在“彩虹重建”平台服侍时,与另一位弟兄轮流撰写每日的灾区事工简报与分析,看见有人说2008年是中国的NGO元年。因为有超过100万的民间志愿者和10万解放军官兵一起到达四川,这是改革30年最了不起的一个成就。而在民间力量的自我动员与参与中,家庭教会又扮演了一个显著角色。当时笔者感恩地写下,“2008年将成为中国基督徒的NGO元年”。
第一阶段的志愿者,很多是受教会差派。随后有了机构的可能性。尽管注册很难,但9月之后留下来的团队,基本上都发展、整合为了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机构。或者注册为公司,按营利性的身份,运作非营利的事工。到2009年初,已很少再有新增的教会差派的志愿者团队。以成都本地教会为例,仍以教会为主体、参与较固定灾区事工的,已是少数。“基督徒爱心行动”、基督徒救助协会、“香柏领导力”、圣爱基金会、“生命力”、“迦南美地”、“帐篷之家”、“牧者心理咨询”等大约十余个机构化的组织,及许多非正式的团队,形成了灾区事工的主要格局。基督徒志愿者不再被整合在教会中,而被整合在机构里。尤其在2009年3月,“香柏”与“圣爱”完成合并,成为跨教会、跨机构同工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在新兴的城市教会,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悔改信主后,他们有着社会参与的强烈意愿,也很容易接受文化使命的眼光。但危机也在这里,因为最热心社会参与的基督徒,恰恰是最缺乏教会生活与委身、顺服之操练的那部分基督徒。也正是新兴的城市教会最缺乏能力与经验去牧养、教导的一群肢体。一位弟兄对此有很好的分享,他说,“我们开会都不知道怎么开,虽然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讲自由、民主,尊重人,结果到教会之后,都吵吵闹闹的。我们特别需要教会生活的操练,和教会治理的建造,在彼此的关系里学习顺服上帝的道。不然开起会来还是一群小共产党员”。
目前,机构与教会的关系、国度化与教会观的平衡,对家庭教会来说是新的课题。第一,机构的社会化和公开化程度,高于家庭教会。加上灾区事工的流动性和灾区同工的混合性,给在机构服侍的信徒接受牧养和参加教会生活,造成了困难。虽然机构的领袖往往来自教会的传道人,但当传道人担任行政职务后,都面临着同工牧养的难题。第二,机构领袖群体的组成,往往来自社会中上层的信徒,教会的背景较弱,甚至可能有一些没有委身教会或缺乏教会观的信徒参与机构服侍。机构和家庭教会的关系也尚未成型。
但机构对区事工的长期果效显然有着决定性影响。第一,灾区事工需要机构,成为福音对生命的改变能渗透和祝福社会的管道。机构需要经过教会生活操练的信徒和在机构专业性上的帮助。第二,教会要以奉献支持机构,而不是由传道人举办社会事工。使教会及其同工清楚自己圣言托付者的职分,免于更深的试探。也使社会事工与宣教事工有更清晰的区分与搭配。第三,在家庭教会的公开性与社会化进程尚且艰难的时候,避免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基督徒在机构发展上,走上与“教会国度化”的异象和教会建造目标相冲突的道路。
圣殿与真道的根基
笔者的担忧与负担,开始落在城市教会的建造与牧养上。因为灾区事工的规模,对家庭教会尤其对四川本地教会而言,呈现出一个落差。就是城市教会的建造速度和在生命在真道上扎根的速度,低于或慢于教会社会参与的速度。这种局面若持续,意味着教会将在未来面临严重的世俗化危机。
地震后的第一阶段,本地教会的同工会基本上不是同工会,而是“抗震救灾指挥部”。在肢体特别需要牧养关怀之时,正是教会的牧养关怀能力大幅下降之时。参与灾区事工,和开放接待其他教会,既给本地教会敞开了大门,也对教会的牧养、治理和教导,带来了挑战与混乱。这也是机构逐渐替代教会,成为灾区事工主体的原因之一。我们可能在将来获得更大的公共空间来表达、传递和见证信仰,这不只是社会政治层面上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也是教会建造、从圣殿到城墙的建造所需要的。主必按祂的心意预备和带来这种变化。仅两三年前,大部分城市教会的聚会还非常保守,慕道友通常是不往主日崇拜中带的。受洗之后,成了“自己人”,才允许参加主日崇拜。这是传统秘密社团的模式。而非教会的模式。但一年来的灾区重建,推动本地教会在这方面的改变非常明显。
怎能不感谢神呢,因为灾难的冲击太大了,所以灾难反而帮了我们。随着教会公开化的突破,随着政教关系转型的可能,也随着基督徒在灾区重建上的持续参与,以及在文化、社会、慈善、人权和公共领域做光做盐、见证基督的空间越来越大。真正的问题开始最集中地,落在了城市教会和灾区教会的建造上。若不能帮助健康、成熟的教会建造,一切参与都非祝福,而是试探。我们理所当然要关怀社会,以真理之光来治理这地,以恩惠福音的传讲来医治这地。但对中国教会来说,文化使命的关键并不在参与本身,而在教会建造上。其实灾区事工的一切难题都与教会的根基有关。中国的基督徒忍耐等候了几十年,只要有点社会参与的空间,自然会跑得很快。所以至少一代人以内,我们都不用担心跑得慢,我们要处理的问题一定都是跑得快带来的。
这样的看见,也是笔者在2008年寻求并最终领受神全职呼召的历程。社会参与的议题,实质就是教会建造的议题。接下来的灾区事工,笔者以为,除了机构的成熟及与教会的关系成型外,最大的难题仍然是家庭教会本身的三个问题。
第一,是建造认信的教会。在地下化的时代,家庭教会普遍轻视信经、信条和大公教会及改教运动的真理传承。但当跨教会的事工和一个“亚社会”的成形,成为神对我们的托付时,面对异端和偏差的分布,及政治制度环境的压力,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和社会化历程,就是一个信仰告白的历程。如在灾区事工的跨教会搭配中,一个常见的考察信仰根基的方式,就是拿出歌本来,我会唱的诗歌,你会不会唱?会唱“同一首歌”的,就是弟兄。但这样的同工,往往无法持久。真道的根基有差异,所见的异象就有差别,属灵观念带出不同的事奉模式,最终无法合一。因为合一不是从诗歌开始的,一定是从真理开始的。信仰告白的运动,就是在真理上合一的运动。合一不是不提我们的差别,恰恰是首先要知道我们的差别在哪里。缺乏这个真理建造的运动,灾区事工就无法在属灵上更深地持续,并成为对教会成长的祝福。这一年,在广大的灾区已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团契和聚会点。但教会在属灵上的混乱和真理上的不成熟,也复制在了灾区教会中。因此目前最迫切的,不是短期的宣教事工,而是信仰的归正和本地教会领袖的栽培。
第二,据笔者了解,本地教会有全职牧者的比例,可能不到30%。求神在城市教会中动工,呼召祂更多的仆人。未来的中国社会,要有更多的基督徒律师、商人、作家,职员,但最重要、最缺乏的,仍然是城市教会的牧者。当四川本地教会参与灾区重建之后,这成为一切事工的瓶颈。在灾区,最缺的不是钱,而是人。最缺的人,不是基督徒,而是有教会生活的基督徒。在委身教会的基督徒里,最缺的,也不是灾区志愿者,而是全职的传道人。对城市教会如此,对灾区教会更是如此。在某个意义上,没有职分,就没有教会。从职分的缺乏上说,城市教会的光景,依然荒凉,等着我们去流泪流汗。
第三,是教会的治理。这一年的灾区事工,从金钱角度说,可能是中国家庭教会有史以来最有钱的一年。少数的团队在奉献的使用上出现问题,更多的团队是金钱没出问题,但关系出了问题,带来同工间的猜忌、论断,和不信任。这在本质上仍然是教会建造的议题。财务的管理、金钱的使用,成熟的制度,交账的负担,这一切的缺乏与试探,都是教会在真理和职分上缺乏后,所带来的第三重治理的缺乏。
然而感谢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这一年,主叫我们倍受激励,也看见社会参与的危机,正是教会建造的挑战。主的心意,必要透过基督徒在灾区重建中的见证,在新的世代赐给中国教会王后的位份,坚固的城墙,和复兴的祝福。
2009-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