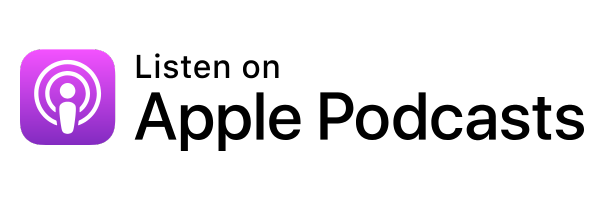12 岁的男孩大卫,从二战后的保加利亚劳改营逃亡,穿越了几乎整个欧洲大陆,去寻找母亲、自由、信仰和“一个有国王的国家”。影片开头,大卫趁着停电半分钟,那一场紧张而静悄悄的越狱,也许是电影史上最美好的越狱镜头。一个孩子非同寻常的逃亡,隐喻着每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看这部电影,是因为读到原著《我是大卫》的中译本。也因为我将为人父,大卫的逃亡与成长,以及电影中这孩子的眼神,实在有一种我在影像和文字中许久没有遇见的光芒。在瑞士,当大卫遇见的那位女画家说,“有人打碎了这孩子的灵魂”。我的心痛,就像心痛自己未来的孩子,以及心痛自己。
1963 年,丹麦作家女安娜•洪在冷战的铁幕下创作出《我是大卫》,将一场从东欧到北欧的地理意义上和政治意义上的逃亡,超越人类的世代,而描绘成一个关于永恒和生命意义上的成长寓言。数十年来,这本书成为青少年成长小说的一部经典。2004 年的电影改编也获得成功,扮演大卫的那位童星演技惊人,在几个电影节上得到新人奖。中译本先在台湾出版,获得了《中国时报》2005 年的“最佳青少年图书奖”。
大卫的父亲是英国人,带着全家去保加利亚帮助抵抗苏俄的扩张。在劳改营中,一个典狱官爱上了大卫的母亲,却处死了她的丈夫,然后帮助她逃亡到了丹麦。在离职的前一个晚上,这位典狱官再次安排了大卫的越狱,他没有告诉大卫真相,只叫他带一封信去哥本哈根。于是这个在阴暗的劳改营满怀忧郁、戒备、“不会笑”的孩子,孤身上路,开始了旷野中的流亡和成长。
电影《耶稣受难记》的主角卡尔维泽,扮演了大卫在劳改营中的朋友和精神导师约翰•尼斯。尼斯告诉大卫一定要逃出去,才能得着美和自由。他对大卫说,从前以色列有一个国王也叫大卫,写过许多赞美诗。尼斯常为大卫背诵另一个大卫的诗,“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大卫问,“他们为什么要把我们关起来呢”?尼斯回答,因为他们恨那些相信上帝的人。大卫气愤地说,让他们去死吧。尼斯摇头,说永远不要这么说,也不要这么想。他帮助大卫学会仰望自己所相信和依靠的力量。在逃亡的路上,大卫发现自己实在一无所有,他对自己说,我也必须要有一个神,好向他祈求。可是在劳改营中大卫听说过各种各样的神,于是他想起尼斯为他背诵的《诗篇二十三篇》,决定从此要向那一位“青草地和安歇之水的神”祈祷。
小说中,大卫的那些祷告非常可爱。假若父母是无神论者,孩子们多半就会把父母当作神,想要什么就向父母开口,并一定要得到。最初的成长,就是当他终于发现父母不是神,不能满足他的渴望,就开始转向其他的“神”,或者接受世界的荒凉。但大卫学会了向他的“青草地和安歇之水的神”感恩,他祈祷说,我很惭愧,现在没有什么可以回报你的。有一次,当他勇敢地冲入火宅,救出小姑娘玛丽之前,大卫祷告说,这一次我不要你帮,让我自己来,给我一个回报你的机会吧,我是大卫,阿门。
到了后来,大卫和他心爱的流浪狗遭遇到一次危难,终于明白了祈祷不是一种交换,原来真正的信心出于白白的恩典,而不是用回报去赚取一个愿望。
可惜好莱坞在一种“政治正确”的傲慢和顾虑下,在电影中竟用一个寓言式的偶像崇拜,替代了小说中的《诗篇二十三篇》。电影里一个面包师给了大卫一个“伊丽莎白像”,说这是面包的创始人,有什么需要向她祈求,她就会保佑你。这一讨好世界的改编成了电影最大的败笔。它将一个孩子的心灵世界简化了,也羞辱了。小说里大卫对信仰和自由的那些孩子般的思考,被好莱坞强行扔进了另一个劳改营。我仿佛又听见大卫问尼斯,他们为什么要篡改我的故事呢。尼斯回答,因为他们恨那些相信上帝的人。
我先看电影,后读小说。电影里的大卫令我心疼得想要收养,但小说中的大卫却更令我对生命的成长满怀敬畏。每个人都要经历他的旷野,亚伯拉罕、摩西、施洗者约翰、使徒保罗,都在旷野的流亡和沉默中得到生命的浇灌。连基督也是如此,先独自经过旷野,再以他的话语返回人群。就如最初的创世,上帝在他永恒的宁静中,用他的话语打破了他自己的宁静。当我低头看一朵花,回首瞥见一个孩子的奔跑,或面向内心澎湃的忧伤,我会禁不住想,这一切就是上帝打破他永恒宁静的表现。连孩子也不例外。专家们称为“社会化”的过程,我称之为孩子打破宁静、走过他生命第一个旷野的旅程。就像大卫穿越整个欧洲,他像一个旁观者,看见每个成年人都活在自己的完整世界里。但对他来说,整个欧洲只是一个旷野,就像艾略特在《荒原》里说,沙漠不只在南方,沙漠也在伦敦桥上。大卫走过乡村、城市,在他遇见的每个人的生命缝隙里钻来钻去。就像在森林里钻来钻去一样。
一个孩子就算天天和父母在一起,他也是旷野里的大卫。是谁的话语,让他进入人群,终于凡事和我们一样?一样相信,或一样不相信;一样的罪,或一样的赦免。一样的月光,一样的日头,照在孩子们的身上。
大卫的逃亡之旅,尽管一切都缺乏,但有三样东西却是他最爱惜的必需品。这三样恰好隐喻了他经过旷野的生命成长,一是肥皂,二是镜子,三是罗盘。
越狱之前,大卫向帮助他的看守开口要的唯一东西就是肥皂。大卫觉得,自由是和清洁有关的。当他在阳光下,用一小块肥皂把“营区的味道和感觉”全都洗掉了之后,他开始觉得自己是大卫。“如果一直有肥皂,我就一直是自由的人”。肥皂成为生命的象征,因为只有被洁净的人才有自由,有自由才有活泼的生命。在电影中是大卫从军官室偷了这块肥皂,军官要枪毙小偷时,尼斯把那块肥皂从他手中抢了过来,站出来替大卫死。卡尔维泽再一次扮演了拯救者的角色,这是一处最精采的改编,使肥皂的象征意味更令人心动不已。
镜子则是真理和智慧的象征。在劳改营中,大卫一直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要到丹麦去寻找什么。他甚至连自己的长相也不知道,因为囚室的镜子挂得太高了。越狱后他开始照镜子,学会了笑。起初,他怀着对世界极大的畏惧进入这世界。但借着一面镜子,大卫慢慢摆脱了劳改营的捆绑,学会了接纳、帮助和信任。镜子促使他思考,当他吃橘子皮时,他说,“如果我连什么好吃、什么不好吃都不知道,怎能说我是一个自由的人呢”。大卫一开始,在别人面前假装自己是马戏团的,后来他发现自己是一个自由的人,因为他有能力思考。他说,“从此我不会再假装自己是其他人了”。
而罗盘显然是道路的隐喻。大卫的第一次祷告,就是当罗盘掉进大海之后。人若自以为知道方向,就不会举目仰望。还一个有趣的情节,大卫在劳改营听人说在欧洲“有国王的国家都是自由的”。他逃亡时便不断问别人,英国有没有国王,丹麦有没有国王。他说,我相信一个国王“不会觉得自己有权剥夺别人的性命和自由”。这不是对一个君主立宪国的浪漫想象,而是生命意义上的一种国度观。这里的“国王”,就是大卫诗篇和哈姆雷特的王子身份所指向的那个“宇宙性的王”。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有自己的国王,和一个灵魂深处的宝座。生命属乎一个灵魂的国度,如果恋爱是寻找白马王子,成长就是寻找一个真正的国王。成长就是从一个国度向着另一个国度的逃亡,从劳改营的为奴之地,向着应许之地逃亡。直到最后在“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得到安息,确定那至高的宝座上,到底是谁或什么坐着为王?
经过了肥皂、镜子和罗盘,大卫越过他的旷野,终于来到哥本哈根,敲响了母亲的房门,有鼻子有眼地说出了这句话,“我是大卫”。
看过电影,读完小说,我又有怎样的确据,说我是谁?有人说,每个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个小秦始皇。一个宇宙性的帝制是人永不可能废除的,当人们推翻了一个紫禁城里的帝王,每个人就在自己的心中登上了帝位。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的紫禁城。我们的孩子呢,要他像我们,还是像大卫?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