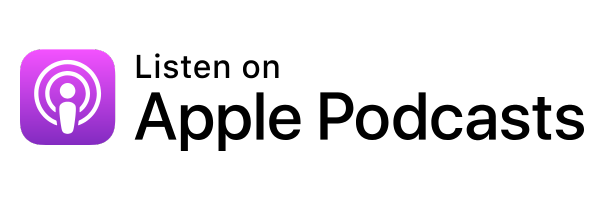这部电影给了世界一个机会,尤其是给我们,看见国家主义这一偶像的黄昏。1989 年的圣诞节,一位牧师在台湾一间教会讲道。有人递了张纸条上来,说“今天,罗马尼亚政权崩溃,齐奥塞斯库被十三名手下乱枪打死了”。1998 年的耶稣升天节,这位叫唐崇荣的印尼华人牧师,在雅加达的教会讲道。又有人递了纸条上来,说“苏哈托今天下台了”。唐牧师举起双手赞美,说“主耶稣啊,你上去,他下来。荣耀归给你”。
曾经,我听朋友唱刘德华和柯受良的《笨小孩》。最后两句是“哎哟往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哎哟向着天空拜一拜呀,别想不开,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笨小孩”。我就问他,老天真的爱笨小孩吗,你怎么知道老天自有安排?这是一种确信呢,还是一种心理学罢了?
其实,只要一个人不是死硬地相信“存在先于本质”,他心里都会有某一种预定论。相信人的意志和选择,并不是意义和秩序的最终决定者。那么在人的行为与终极意义之间的那个空间和落差,就是属于预定论的。捷克“七七宪章”的领导者之一,剧作家哈维尔,曾在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对外在强权的真正的反抗就是“活在真理当中”。他并不是一个宗教信徒,但他强调说,“我从小就感觉到有一种高于我的存在,那是意义和最高道德权威的所在。在‘世界’的事件后面,有一种更深刻的秩序和意义”。他把这个背后的秩序和意义,称之为“绝对的地平线”。
在哈维尔看来,这就是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参与者站在世俗的立场上反对一种世俗的公共权力,而“没有能力将自己从表象的世界中彻底解救出来”。换句话说,他们与他们的反抗对象一样,认定在人的行动以外,历史一无所有。
捷克文学的翻译者景凯旋先生,把这种对最高存在及其秩序和意义的敬畏,称之为“捷克思想中最崇高的那一部分”。在波希米亚,这一近代传统的源头,来自宗教改革的先驱,伟大的捷克改教家和殉道者胡斯。胡斯拒绝一个笛卡尔式的和二元论的断裂世界,他回归圣经,坚持一个古旧的和完整的宇宙图景,仍然把“世界”看作一个整体,认为秩序与意义的根源,乃至人类历史的展开,既不决定于人的主观,也不决定于人的行为,而是决定于那个超验的、智慧与爱的存在,即自我启示为“I AM”的那一位。
“七七宪章”的发言人,捷克哲学家帕托切克也说,承认普遍人权,就是“深信国家和社会必须认可某些高于它们的绝对的事物,某些即使对它们来说也是受制于此的、神圣和不可侵犯的事物”。但这一点,恰恰是苏联当初不同意《联合国人权宣言》第一条的理由。尽管有许多国家的代表,说他们不相信基督教的创造论,于是草案中的被造自由平等(created free and equal),最后改为了“人人生而自由平等”(all human beings are born free and equal)。但苏联代表团还是投了弃权票,他们说,我们的国家“不承认一个获得国家公民地位的人,独立地拥有个人权利这样一种准则”。
换句说话,苏联认为,国家是一切个人权利的来源。没有比国家更高的价值,就算有,也一定锁在总书记的保险柜里,不可能在其他地方。于是国家僭越了上帝的地位,把一个“人”变成了一个“公民”。革命被称为“开天辟地”,建国就等于一部《创世记》。在这样的观念下,当你被称为一个公民,意味着国家是你的造物主;你的身份,是它的一个产品。
这样就能理解国家主义为什么是一种偶像崇拜。为什么一个不愿认可普遍人权的超验性,换言之就是不承认“老天爱笨小孩”的国家,一定是专制主义的国家。以及为什么在这样的国家里,一定会有铺天盖地的“窃听风暴”。
当国家扮演了“自有永有”的那一位,它就接着扮演“全知全能”的那一位。
让我再次缅怀那一天吧。1989 年 12 月 29 日,哈维尔从狱中放出来,当选为捷克的临时总统。半个月后,成千上万的东德民众如决堤的洪水,从 40 余处入口涌进了国家安全部的院子。他们把负责国内监视与窃听行动的办公室砸个稀烂,将浩瀚的秘密文件和档案从窗户抛出去,铺满了大街。
令人感佩的是,16 年过去了,和我同岁的多纳斯马克,不动声色地自编自导了他的处女作《窃听风暴》,获得 2006 年德国电影奖 7 项大奖,和欧洲电影奖最高大奖,以及 2007 年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我几乎一开头就爱上这部电影,熄灯之后一再为它唏嘘。也忍不住推荐给我认识的每一个知识分子。
2006 年 11 月,原东德国安部的副部长沃尔夫,在这部电影获奖后不久去世。沃尔夫在自传中说,他的理想是通过社会主义,使德国永不再重蹈纳粹的覆辙。如今虽然失败了,他说我依然怀着如此的信仰。在他的“信仰”背后,是东德国安部雇佣的 9 万名特工(OM)和 17 万 5 千名线人(TM)。它甚至监控了 1700 万人中的近 600 万。当柏林墙竖起的近 30 年间,平均每天就有 8 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两德统一后,国安部的全部窃听档案,移交给了新成立的“高克管理局”,开放给所有公民查阅。这些监控资料若一本本铺开,将有 1000公里长。它的被公开,掀开了人类史上一个最残酷的撒旦的盒子。无数人发现自己的同事、朋友、律师、医生甚至家人,都是国安部的告密者。这个社会要以多大的勇气,去承受前所未有的道德打击与罪的折磨啊。曾有一对夫妻双双自杀,因为多年来,他们彼此都向秘密警察出卖对方。
1989 年的柏林墙,多纳斯马克和我一样还是中学生。我能体会一个“后柏林墙”时代的青年人,为何能拍出这样椎心刺骨的创伤。因为我的忧伤也与他一样。但他的盼望也与我一样吗。我最关心的,是多纳斯马克能拍出一个不虚假的盼望吗?黑暗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残酷已经残酷到了家。所以电影开始五分钟以后,我就一直期待着对我而言最大的悬念,这样的电影,会将一种有说服力的盼望放置在哪里?
影片的每个镜头都很冷静,每个画面的色调都落入灰暗。但感谢上帝,这部电影并不是潘多拉盒子的一个继续。当多纳斯马克还是电影学院的学生时,一天在家听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他忽然想起这曾是列宁最喜爱的曲子,列宁说:没有比《热情奏鸣曲》更美的音乐了,惊人、超寻常的音乐!它总让我像幼稚的孩子一样由衷地觉得自豪——怎么人类可以创造出这样奇迹似的乐曲。
但列宁仿佛忽然清醒过来(或者糊涂过去),接着说:
但我不能常听这个乐曲,因为它会影响我,使我有一种冲动,想去赞美那些活在污秽地狱里而仍旧能创造美的人,想去亲抚他们的头。可是这个时代,你不能去亲抚他们的头,除非你希望让你的手给咬断。你得重击敌人的头——毫不留情地重击——虽然说,理论上我们是反对暴力的。
当时多纳斯马克已访谈了很多当年的秘密警察和线人,为他的剧本做功课。他渐渐发现,那些秘密警察和列宁一样,“是一群把内心情感上了锁的人”。列宁克服对一首曲子的感动,因为“他害怕他的感情会破坏他对原则的追求”。就是说,他知道他的原则乃是反人性的,但却着了魔地无力自拔。
多纳斯马克想,如果革命家和他们的秘密警察,可以敞开心扉地去听《热情奏鸣曲》那样的音乐,这个世界会不会不一样?于是他带着这个具有“伦理上的想象力”(崔卫平)的念头,去面对人性在制度下的悲凉,并将出人意外地把温暖放在了那个窃听者身上。这个一出场就冷血无比的上尉警官魏斯勒,负责监听异议知识分子们的言行。他全天候监听剧作家德瑞曼和他同居的女友、一位著名女演员的生活。监视,使被监视者的苦难、软弱和对爱与自由的盼望,逐渐打动了他。一天,他偷走了德瑞曼摆在桌上的诗集,躺在孤零零的沙发上,读到这样的句子:
我们头顶干净的天空
一朵云慢慢移动
它那样纯白,那样高
当我再度凝视,它已消失
但只要你从心底相信
它就一直在你身边
生活在沉没,鸽子仍在飞翔。德瑞曼的一位导演朋友自杀后,他坐在钢琴边,弹起了《热情奏鸣曲》。而魏斯勒是唯一的听众。德瑞曼得到了西德媒体提供的一部微型打字机,准备写一篇政论,评论东德政治高压下的知识分子自杀问题。文章暗地里交给《明镜》周刊发表,揭露东德自 1977 年开始就不再统计自杀数字,社会主义国家中只有匈牙利的自杀比例高过了东德。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小小的地震。但魏斯勒从报告里删去了打字机的故事。他开始暗自掩护这位作家躲搜查和迫害。直到 1989 年后,德瑞曼遇见前文化部长,他天真地问,为什么那么多人被监听,被带走,我却没有呢?部长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你的全部生活包括每一次做爱,我们都一清二楚。德瑞曼被震惊了,他回家去,把埋在墙壁里的线一根一根的拉了出来。后来,他在“高克管理局”查到了代号 HGW XX/7的魏斯勒的监视报告,并将自己的新书《好人奏鸣曲》题献给他。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窃听会改变一个秘密警察的道德抉择。起初,在电影中我看到三个理由。一是细节的真实,二是美善的毁灭,三是历史的提醒。
我以为,被监控者真实的生活细节,对秘密警察的工作性质构成了一种颠覆。德瑞曼和他的女友不知道自己被监控,他们的一切都逼真到一个地步,连他们的痛苦和羞辱,也使一个偷窥者察觉到自身的虚无。而另一种尖锐的力量,就是看着一种美怎样在你面前毁灭。女演员最终向文化部长妥协,以她的肉体去逢迎一个黑暗的世代。德瑞曼与她在卧室的一段对话,令魏斯勒颇受震动。当女演员被捕后,魏斯勒亲自对她进行疲劳审讯。当她终于开口出卖她的情人时,你甚至会想,魏斯勒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失望的那个人。他不能容忍他监控的对象,背叛那个他不能企及的“头顶干净的天空”。女演员的软弱和背叛,再次刺激了魏斯勒,催逼着他挺身而出,继续掩护这位作家,也在德瑞曼的面前掩盖了女友的背叛。女演员冲出房门自杀,临死前对这位毁灭了她生活的人说,“我不会忘记你所做的一切”。魏斯勒告诉她,“我已经把打字机转移了”。
最后一个戏剧性的扭变,魏斯勒本来准备汇报德瑞曼的打字机计划,他的上司却偶然谈起被监控的四种人的理论。他说,你窃听的这个属于第三种,叫作历史性人物。千万不要和他们有任何正面接触,不然你会被记在历史当中。这句话的意思,就和列宁不敢多听贝多芬的音乐是一样的。这是多米诺骨牌的最后一张,将一个政权在历史、正义和灵魂面前的虚弱赤裸裸地表白出来。那个在历史中将高于一切人为的秩序和价值,那个“老天爱笨小孩”的信念,给魏斯勒卑微的命运壮了胆,带来一个理想主义的维度。他悄悄收起了报告,表情冷漠地,决定站在被称为“历史”的那一边。
但有这三样还是不够。诗句只能颠覆诗句,不能颠覆价值。音乐也是如此。所以我不想过于夸大布莱希特的诗歌和贝多芬的音乐,对魏斯勒的灵魂做成了什么。在基督徒看来,艺术源自造物主的普遍恩典。真正的审美,如果不落入一种偶像崇拜的话,审美一定是位格者之间的生命相交。那一位有位格的上帝,在一切地上的活物中,仅仅赋予了人以位格,上帝的“形象和样式”就包含在这位格里面。一个人就算怎样爱他的狗,人狗之间也不能有生命的交通。因为动物没有位格。人的生命只有两个爱的方向,也是两个美的方向。一是人与上帝,一是人与人。基督说上帝的一切诫命,都包含在“爱神”和“爱人”这两个原则里。反过来说,圣经所说的“爱”的外延,就是对神的爱和对人的爱。世上没有第三种爱。
上帝不让我们“爱”任何非位格性的存在。“国家”没有位格,所以上帝不要我们是“爱国主义者”。狗没有位格,金钱也没有位格,所以上帝不要我们成为拜物主义者。山川湖海都没有位格,所以上帝不要我们成为自然主义者。对着一块木头说我爱你,那不是“爱”,那是偶像崇拜。偶像崇拜就是我们自以为的“第三种爱”。
有许多哲学家如洛克和边沁,曾列举过人类的十几种主要情感,其中都没有“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因为在欧洲,这种非位格性的情感,原本就是“上帝之死”和“国家崇拜”的产物。当我说,我爱这片土地,我委身于我出生的中国。我爱的到底是谁呢。乃是与我一样黑头发、黄皮肤的人所组成的一个族群,以及这个族群在彼此位格的交往中所形成的那个空间,包括社会、文化、艺术、市场,也包括政治。如果从神学上理解民主政体的正当性,我首先看它是一个“位格”议题。所谓“民意”,就是位格相交的重叠。政治与艺术一样,当它不悖逆超验价值的时候,都是人的位格相交的一部分,被包含在 “爱人”的里面。
位格的真实性,也带来位格者的独特性,就是那无法被他人所取代的“临在”。当我们欣赏一幅肖像画,或贝多芬的音乐。艺术家虽不在现场,但他们透过其作品“临在”。就如使徒保罗,虽未亲笔逐字写下书信,但他总在信的末尾加上亲笔问安,延展他本人位格的临在。我们透过这“不在场的临在”,而能与另一个生命有愉悦的相交,这就是审美。这样审美也有两种,一是与另一个人的位格相交,品味生命的一种丰盛。二是欣赏非位格的存在时,借着造物主的这件作品而与他相交,品味另一种生命的丰盛。
然而,若将抽象的“国家”或国家主义当作爱与忠诚的对象,就不是爱国,而是偶像崇拜。若是拿着皇帝的尚方宝剑出来,说“如朕亲临”,就不是位格的延展,而是偶像崇拜了。若是爱动物爱到禁止穷人吃肉的地步,也不是治理这地,也是偶像崇拜了。若是梵高的一幅画可以卖到上亿美元,就差不多与梵高的位格无关,也不是审美,而是恋物了。
为什么一个革命家害怕听《热情奏鸣曲》呢,他害怕的,就是与贝多芬的灵魂迎面相遇。他敢闭着眼睛杀人,却不敢与一个如此独特的生命保持位格的相交。就如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不敢将他们的灵魂赤露敞开在那一位神的面前,就开始在园子里东躲西藏。他们也不再向对方彼此敞开,于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
的确,在《热情奏鸣曲》这样的音乐面前消灭心灵感动的人,大概就向着地狱坠落而去了。但是人与人的位格相交,就算如何感动,也不能将一个罪人救拔出来。真正对魏斯勒构成颠覆的,是在秘密窃听的状态下,一个人的生活那样逼真,那样全息。这样的窃听使魏斯勒坐在了一个全知全能者的位置。一个专制政府的大规模窃听,是国家主义对于上帝的继续冒充。窃听是国家将自己当作宇宙主权者的结果,它需要窃听它的公民,需要一个在预定论中全知全能的地位。因此它也以窃听来替代新闻自由,因为这种被冒充的全知,须以被窃听者的无知为前提。就如《论语》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魏斯勒在这一体制中成为一个窃听者,他与那个他本不应该坐上去的位置,就构成了一种奇特的位格相交。
就如一个偷情的男子,他不仅与他的偷情对象发生位格的关系,他也和那个被他冒充和顶替的丈夫,发生着一种位格的相交。那个丈夫尽管不在场,却“临在”于只属于他的、那个独一无二的身份里面。所以摩西十诫的最后一诫,在归纳人与人的关系时说: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拜偶像,是把上帝从你心中的宝座上推下去。而贪恋属于别人的东西,则是把别人从他的身份和位置上推下去。有一部法国 1982 年的电影《马丁·凯尔的归来》,好莱坞的翻版叫《似是故人来》。一个相貌和桑马斯比酷似的囚犯,出狱后来到桑马斯比的家乡,冒名顶替,接管了“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他努力成为一个好人,帮助他的乡亲,爱那个不属于他的妻子。最后,有人告发桑马斯比曾经杀人,将这位冒名顶替者判了死刑。他的“妻子”在法庭上作证,说他并不是桑马斯比。但他竟不愿意以此脱罪,最后甘心情愿的,以“桑马斯比”的名义走上了绞刑架。
当我在位格的议题中理解秘密警察魏斯勒时,我也理解了多年前的这部电影。为什么“历史的审判”会构成对魏斯勒的一种提醒?假如要举人有位格、而狗没有位格的一个例子,就是只有人才会有“中年危机”,或者“身份的焦虑”。因为唯有人才有历史的意识,“时间的经过”唯独对于有位格的人才有意义。“我在历史中的身份”,是唯有位格者才有的反思。这也是推动魏斯勒和“桑马斯比”作出个人道德抉择的力量。
所谓“中年危机”就是人在历史向度中的困境。只有当现今的每一刻都是真实的,“当下”对于过去和未来才具有意义。也唯有一个位格者,会在每一个当下停顿和联结,去处理当下与永恒的关系。换句话说,借着位格的相交,永恒也“临在”于我们的每一个“当下”。因此生命的更新与倒转的可能,也在每一秒都是向着恩典开放的,等候着永恒者的浇灌与模造。哪怕是我们临死前的那一秒钟。所以一个人临终前的祷告与盼望,与出生后那一刻的盼望相比,也并没有丝毫的减少。
“桑马斯比”冒充的是一个人,魏斯勒冒充的却是上帝。魏斯勒对监控对象的“全知”,产生了一种“全能”的责任感。他开始利用他的信息,介入甚至“预定”德瑞曼的生活。当他发现文化部长送女演员回家,在汽车里侵占她。他以一个电话,把德瑞曼引出门,发现了女友的私情。当女演员哀伤地离开家,准备继续与文化部长约会时,他在酒吧与她“偶遇”,以一个忠实观众对她艺术的热爱,激发她转身回家。对德瑞曼来说,他被全面窃听的生活,真的是被“预定”的。因此他写书献给魏斯勒——这一位转恶向善的护理者,和他生命中“那一只看不见的手”。
魏斯勒的选择,不仅是一种“伦理上的想象力”,而是生命里永远临在的奇异恩典。也是他对一个僭越的位置的忏悔和赎罪。尽管这还不是真正的救赎。
这部电影关乎苦难,也关乎盼望。扮演魏斯勒的演员乌尔里希·穆埃,也同时获得了德国和欧洲两个最佳男主角奖。最令人心酸的是,他答记者时说,“因为我的妻子,曾经就是国安部的告密者,长达六年向政府汇报我的情况。这不是别人的生活,这就是我自己的生活”。
感谢上帝,他的语气很平静,就如电影的镜头一般。那些和我一样大的中国作家,一样大的中国导演,他们都在哪里呢?我不由打量四面的墙,心想每个人都活得如此逼真。就算报道说,东德的秘密警察中并没有出过魏斯勒这样的人,就像刑满释放犯里也可能没有出过“桑马斯比”这样的人。但我仍然相信,任何一种生命的倒转都是可能的——在生命的任何一刻。不在于你敢不敢听贝多芬,在于你面向自己的罪,有没有捂住耳朵,不敢与圣洁的那一位迎面相遇。如果魏斯勒是这世上绝无可能的一种人,那么监控的人失败了,被监控的也失败了。连纳税人的钱也就这么浪费了。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