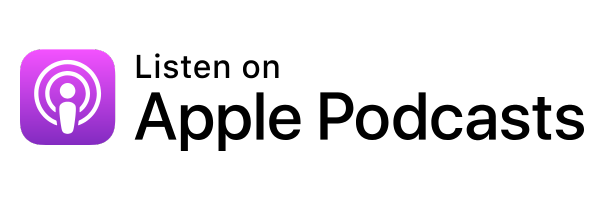239
葛瑞格·达彻(Greg Dutcher)是一位相信加尔文主义的牧师,他写了一本耸人听闻的小书,《谁杀了加尔文主义》。按他的说法,加尔文主义,和加尔文主义者,正在成为一对反义词。
240
根据恩典的教义,这也是不难理解的。恩典,与承受恩典的人,就是彼此反动的。我的意思是,抗拒恩典,就是我们这些蒙受恩典之人的自然倾向。我说的“自然”,就是全然败坏之罪人的自然。
如保罗所说,重生的人里面,有两个律。老我与新人,情欲与圣灵,永远在我们身上相争。信心,就是相信这场相争,必然(甚至已经)在基督里得胜了。这种得胜是一种被替代的得胜。
如果我们的刑罚被代替了,我们的得胜也在被替代中被确定了。
但我们在一个相信的过程中,却是始终不信的。我们的降服,始终是不情愿的降服;我们的相信,始终是不能相信的相信。
241
让我这样说,一个相信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人,当他说他相信的时候,他是在不信中相信。当他说不惧怕的时候,他是在惧怕中说不惧怕;当他说我愿意的时候,他是在不愿意中说我愿意。
换言之,因为他明白福音,所以他相信一件事,就是相信他本人的意志不值得相信。
242
所以,我渴望为主殉道吗,我渴望为福音而死吗?我知道我里面极其渴望,如保罗说,我情愿被浇奠。但我同时也知道,我里面并不情愿。一个不情愿的力量,始终在主所赐的情愿中。这就使我知道,我的情愿,并不出于自己。
在某个意义上,我的信心和情愿,因为是主所赐的,所以可以被称为是“我的”。但又因为是主所赐的,是外在于我的,就是外在于我的“旧人”的。因此,又不能完全被称为是“我的”。换言之,用保罗的话说,我不能说我“现在”、“已经”、“完全”得着了。
243
因此,我知道,在某个意义上,我与我所承受的救恩之间,仍然是一对矛盾。相信这个救恩,的确是我的信仰;但抗拒这个救恩,也的确是我的现实。抗拒是现实的一部分,甚至是“信心”之所以具有价值的那个现实。
同样的,我也知道,我与我所持守的教义之间,也是一对矛盾。如果说,我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那么,这既意味着,我本人是加尔文主义的信奉者;同时也意味着,我本人就是我所持守的加尔文主义的敌人。
244
天主教会因此争辩说,你不能单单因着“信心”,就宣称自己已经得着了。他们认为,“得救的确据”是不可能的。若有人如此宣称,他是在自己骗自己。
改教家们却坚持,称义不是被“注入”的,而是被“代替”的,或者说在替代中被“归算”的。如果“义”是因神的恩典注入我们里面,就像武侠中的顶尖高手,将内力输入年轻人体内。
这个年轻人就必须试着一掌击出,发现他能摧毁一棵树。他才能确定,自己确已拥有了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内力。
这样,在天主教会那里,“称义”就和“成圣”连接以来了。称义就是成圣,成圣就是称义。一个人若还在相信的时候怀疑,在顺服的时候抗拒,在圣洁的行为背后仍存有污秽,那么他怎么可能(怎么敢)确定,自己是一个被救赎之人呢?
245
然而,又有谁不是在相信的时候怀疑,在顺服的时候抗拒,在刚强的时候软弱,在圣洁的行为背后仍存有污秽呢?
如果天主教承认,事实上,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可以在活着的时候,透过他的完美的成圣,显出他的完美的称义来。
那我们之间,就没有太大的冲突了。但不幸的是,天主教会居然认为,真的有人可以不在相信的时候怀疑,不在顺服的时候抗拒,而且在圣洁的行为背后也不再有一丝污秽。
那我们就必须将这句话奉还了:若有人如此宣称,他就是在自己骗自己。
246
义是因基督的代替而被“归算”的,而不是“注入”我们里面的。这意味着(按着西方教会特有的法学思维),“称义”是
一个法庭上的宣判,是关乎一个人在永恒至高的上帝面前的法律地位。
福音的意思是,上帝首先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地位,新的身份。而新的性情,新的样式,必须从这个新地位上活出来。因此,一个还没有活出属神性情的人,仍然可以是神的儿女。而且,他必须先是神的儿女,才可能活出儿女的神态。
如果你收养一个孩子,你不可能对他说,你先叫爸爸,你叫了,我就收养你。他即便这样叫了,也不是怀着“儿子的心”,而是怀着“奴仆的心”叫的。你必须先收养他,成为他的父亲。
然后,他才会渐渐活出儿女的样式。如果你是一位君王,那他必将活出王子的样式。
247
这就是恩典的意思。恩典在本质上只取决于施恩者的意志,不取决于蒙恩者的表现。基督的代替性的赎罪,是一个罪人在尚未完全清除他的罪行之前、而被称义的唯一根据。因此,“注入”的观点,本身就是与恩典相反的。因为“注入”的观念,如此强烈的要求一个结果,要求一个验证,要求一份被注入者的成绩单。
248
相反,“代替”和“归算”的义,意味着上帝,不那么急着看我们的成绩单,他给了我们漫长的一生来挣扎,来怀疑,来软弱,来抗拒。因为在终极的意义上,我们的成绩单是被注定的。
虽然圣经不断警告我们,勉励我们,也劝戒我们,竭力活出属神的性情,预备去行一切的善事。但如希伯来书所强调的,这不是一场淘汰赛,而是父亲对儿女的管教和训练。成圣,恰恰必须在与“称义”完全无关之后,才会成为可能,并充满活力。
249
唯独因为成了肉身,又被钉在十字架的基督,就是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完成了义对不义的代替——路德称之为“甜蜜的交换”。保罗如此令人震惊的,将福音的实质表述为“称罪人为义的神”(罗4:5)。
250
当我说,我作为加尔文主义者,正是加尔文主义的敌人。我相信福音,但我本人在离世之前,永远是与福音相反的。即使我的属灵生命有了长足进展,只要我一天还活着,我就是福音的敌人。
换个说法,就是福音的改造对象。这意味着,每一天,当我意识到自己仍然是一个抵挡福音的罪人时,神对我来说,就仍然是、和正在是“称罪人为义的神”。保罗接着说,信这位神,“他的信就算为义”(罗4:5)。
251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约翰·派博说,“神就是福音”。关于我的生命和整个宇宙,最大的好消息,就是竟然有一位“称罪人为义的神”。
252
也正因为如此,保罗晚年劝勉提摩太时说,“我儿阿,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后2:1)。而不是说,你要在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刚强起来。
这和彼得晚年劝勉下一代的口气,几乎一模一样。“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彼后3:18)。
因为一个基督徒若不在恩典上长进,无论他作了什么善工,又无论他的神学是多么加尔文主义,他的生命就根本没有长进可言。
253
理性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道德主义。因为理性主义假设了,你就等于你的思想。或你的教义就代表你的生命。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但我们也可以说,你就等于你的祷告,你就等于你的奉献,你就等于你的侍奉。而道德主义的意思,就是将一种“荒谬的信心”(因为属天,所以荒谬;因此出于神,所以不可理喻),与一种可以评估、外显和比较的人身上的外在记号,连接起来,建立一个因果关系。
254
因为教义是可以习得的。有人持守某种正确的教义,有人践行某种正确的善行,这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都可能出于邪恶的目的和复杂的动机,因此并不能被称之为“善行”。
但改革宗传统的最大危险,就是理性主义的危险。即将持守一种正确教义的行为,视之为“善行”的可怕倾向。“我相信被称为加尔文主义的恩典教义”,这件事的属灵意义被理性主义化了,或者说被拔高了,被偶像化了。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我相信被称为加尔文主义的恩典教义”,仅仅是我的一部分事实。而在冰山的下面,“我相信恩典的教义”这件事本身,其实是我抗拒恩典的一种方式。
255
但愿圣灵常常提醒我,加尔文主义的主要敌人,不是改革宗教会以外的人,而是那些相信《威斯敏斯特信条》的人。
但愿圣灵常常提醒我,对一个改革宗信徒来说,认信《威斯敏斯特信条》是正确的和重要的,但这不是改革宗人士称义的方式。我们和一切出于各种原因而不接受《威斯敏斯特信条》的基督徒一样,都是单单因着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基督是主而称义的。
——摘自《宗教改革沉思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