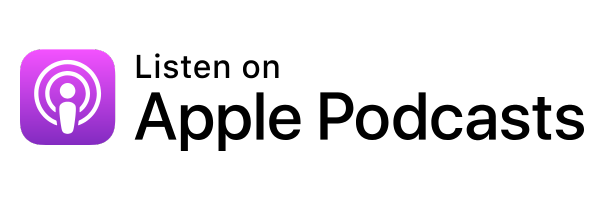我选了这两种鲜花,追思告别后,跟家人一起,和岳父的骨灰一道,撒在一段江面。
恰好是我和妻子初恋常去的那一段。筑坝之后,江面拓宽,原先我们坐在那里的草地,已不见了。吻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我在那时写下诗句,“吻你时我发现人类的无力/梦想上帝把你还原为我的肋骨/当初亚当和夏娃是如何离开的/那个晚上。我们像领取圣餐一样开始接吻/并在内心坚信,我们的子孙/终将回到赤身露体的园子”。
那样的年龄,怎能想到,生有时,死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岳父的骨灰,十几年后,也将从不远的水面漂走。人类筑坝的动机,也不过是想挽留更多的东西。在宽阔的水岸,我们像富足得不肯松手的人,却终将有限的身体,投入流动的江河。江河能去哪里?《传道书》说,“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譬喻,人归了他永远的家;尘土仍归于尘土,就像江河仍归于江河。但灵魂,却归于赐灵魂的上帝。
所以,撒去骨灰,不是对生命归宿的一种确信,是对循环往复的一种文学性的处理手法。同一天,我收到廖弟兄娃儿降生的短信。早上醒来,端过儿子的脸,在晨光之下,有一种生命的气息,彷佛仅仅是属于这一天的。我以往未曾见过,我对小书亚说,送走了外公,你就长大了。
一周前,收到艾晓明制作完成的这部纪录片。关于地震中失去的娃娃,看过不少民间流传的影像。但这份记录,沉甸甸的,又将我带回 512 后的那半年,渐渐听见上帝对我传道的呼召。
教师,是一份在死亡面前无法自持的职业,就像儿子是一个在父亲死亡时无法自持的名分。13 年前,我在大学任班主任的第一个学期,有个女生,班上的学生委员,怪不好意思的,提着一盒月饼来我宿舍。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有人送月饼。多年之后,我遇见一个学生,告诉我,那个女孩因为恋爱,遭家里反对,就悬梁自杀了。
那个晚上,我哭了很久,因为忽然意识到,她之所以送我月饼,和她自杀一样,都是不情愿的。只是其中绝望的程度不同罢了。倘若我所言所行,都要影响人的灵魂,那么教师就像法官、祭司或君王,根本就不是人可以干的。谁能穿上那身衣服,谁能登上那个宝座,谁能站在那个讲台呢。
如果人有灵魂,我怎敢做人家的教师,我也不敢做人家的儿子。如果没有上帝,我就无法将那个女孩的死,和我作为她老师的身份在因果律上彻底撇清,也无法将我与我亲人的死做个了结。许多人都有自怨,说自己倘若如何,他(她)就不会死了。心理学在这一层面都是自欺欺人的。逻辑上说,只有两种情形,可以撇清你与他人死亡的干系。其一,世上万事都是一个绝对的偶然,因为秩序的缺乏,就取消了人的道德责任。其二,有一位上帝,在他绝对的旨意中成就万事,各按其时。
意思是,第一种情形下,你的悔恨全无用处;第二种情形下,你在悔恨之上能够选择信靠。两种之间呢,是我明明看见了某种因果,却无法相信更高的原因。这等于把我的作为,摆在了一个至高的、被问责的地位。我的良心,如何可以承受煎熬,卸下重负?
一个教师不相信上帝,他一开口,就一定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当做真理的代言人。一个政府不相信上帝,他一动粗,就一定在某种意义上把自己当作了权力的图腾。我看了这片子,忍不住将离世的岳父,和垮塌校舍下的娃娃做个对比。尽管亲疏有别,我的伤痛,仍难分轩轾。不过地震若非在四川,对台湾风灾的罹难者,我就淡漠得多。一周前为灾区的祷告会,我心口子痛,想起一年前的委身,惟愿大地的余震,永远在我灵魂深处不断绝。如今的安逸,彷佛 8 万人都白白死了。孩子们的死,若没有迟到的公义,怨恨的力量,就大过地震波,仍在灾区蔓延,直至人心深处。从社会学的角度说,最好的心理辅导,就是公共责任的追究,与真相之上的忏悔。不然,每天做三次深呼吸,躺在治疗床上倾诉一小时,于人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
上帝的恩典与怜悯,永远伴随着对人的追问,而非对遗忘与虚谎的宽待。还有差别,岳父经过一生,死于癌症,他的死是家事。娃娃们殁于天灾,又纠结于人祸,他们的死是天下事。
但奇怪的一点,尽管死于校舍垮塌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给了人们最大的道义感染力。独生子女在这个时代的价值观中,也有着极昂贵的地位。但一年来,这仍未能成为一个极具重要性与延伸空间的公共事件。就像毒奶粉事件那样,慢慢就从天下事退回了家事。
说到底,中国人的灵魂观是建立在惧怕之上的。鬼神也放在一起说。许多出租司机不愿到殡仪馆;尽管机会都一样,人们通常也是参加婚礼的多,参加葬礼的少。一个小妹妹说,这里好恐怖,害得小书亚把这新词汇念叨了几天。我在想,这种观念导致了一种私人情感与公共领域的错位。譬如从人情世故说,父母失去未成年儿女,哀伤程度通常都大于成年儿女失去父母。但儒家传统的“五服”,却不根据私人情感来论定,它非要把失去父母的哀伤拔高,把失去子女的哀伤降低。
这是在背后,把对灵魂之结局的畏惧,当作了治理的起点。王充在《论衡》中,倒很尖锐的指责孔子。他说孔子其实不真信死后有鬼。但祭祀礼仪的目的,是为了威胁臣子。假如不祭祖,说人死如灯灭,乱臣贼子就多起来了。人们公开流露的哀伤,区分为不同规格,这种风气于今仍盛。所以校舍垮塌事件的实质,是家长们的集体哀伤打破了这种潜规则,危害了和谐社会的政治秩序。王充说,所以“圣人惧开不孝之源”。向上的维度,装神弄鬼是必须的。向下的维度,就难免冰冷了。
我们的娃娃,在家长那里等于一切,在公共政治上等于零。如同孔子一样,掌权者并不真信人有灵魂。他们的手法和民间宗教的祭祀差不多。就像一个长辈特别嘱咐孩子们,送骨灰的时候,千万不要回头望。
我们对吓得半死的小侄女说,爷爷以前是无神论,现在相信上帝,不相信鬼。你若知道人的灵魂要去哪里,你就不怕人家装神弄鬼。
2009-10-20,完稿后一分钟,凌晨 0:44,北川和平武交界处(北纬 32 度,东经 104.5 度)再发生 4.9 级地震源深度为 20 千米,在成都写字台摇动,震感强烈。
——摘自 灵魂深处闹自由:《与神亲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