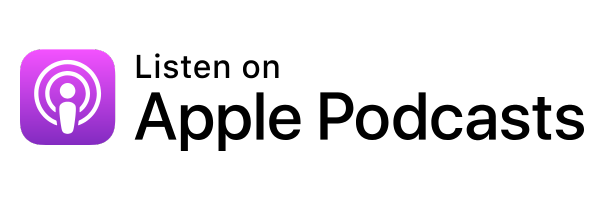杨:后来,三自的口号很清楚,就是要“爱国爱教”,你是不是考察过,究竟这个口号是共产党提出来的,还是教会人士先提出来的?
王:我没有读到很明确的史料,但基本的一个脉络,从51年到54年,最初的口号是“三自反帝爱国”。这是三自运动的第一个阶段。直到文革结束,1980年代初,三自复出,“反帝”就去掉了,变成了“三自爱国”,是三自运动的第二个阶段。这时,“爱国爱教”开始提出,成为第二个阶段的三自口号。这个起源肯定是中共中央1982年的19号文件。因为里面明确提出要“恢复爱国宗教组织”,多次强调“爱国”是新时期宗教统战工作的焦点。“爱国爱教”不过是三自内部对此的回应。至于是主动的,还是高人授意的,不太清楚。
杨:这个口号现在到处都有,随时可以听到,而且各大宗教的爱国会都接受。爱国爱教,听起来挺好,但是爱国第一,爱教第二。而且耶稣讲,诫命有两个总纲,就是爱神爱人,没有说爱国,也没有说爱教。这个张力怎么处理?我们再回到50年代,是不是可以说,因为那时中国基督徒思考自立的问题,已经思考了30多年,这时有一个新政权出现了,这时自立的教会与新政权是什么关系?合作?还是对抗?还有其他方式吗?可不可以这么说,有人在策略上选择了合作,这样求得生存的空间。另外一些像王明道这样的人说,我没法合作,如果合作的话,就失去了真实的信仰和自我,那他们就只好进监狱。可不可以他们都面临一种策略选择,而不同的策略选择导致了不同后果?
王:不单是教会,包括知识界,反思57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时,也有类似的思考,譬如策略上的衡量。也有很多人说,他们当初的选择是真诚的,后来的懊悔和反思也是真的,所以知识界就说是“两头真”。但我认为王明道的那些文章,讲述了一个神学上最根本的东西,他为什么不跟吴耀宗他们合作呢?王明道不是说,吴耀宗是个小人。他是策略上的委曲求全,他是想抱共产党大腿,等等。不,王明道直接从信仰的逻辑作出判断,说吴耀宗是“不信派”。事实上,他称整个三自运动叫“不信派”。在王明道看来,四十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真信。他们之所以做出策略上的选择,是因为他们骨子里的不信。
这个不信是很大的一个时代背景。上个世纪2、30年代,不单中国,整个西方社会都叫做“粉红色的年代”。不但一方面基督信仰开始衰退,另一个方面就是对于国家主义,对于崭新的社会革命,对于建立一个美丽新世界,整个全世界从东到西,都充满了梦想。一种达尔文式的文明进化论的乌托邦。即使经过苏俄的惨剧,英美社会还是全面走进了一个左翼世界,就是很强烈的要透过国家、透过政府去成就更宏伟的国家目的。在这个国家目的里,“或男或女,或自主的或为奴的,都成为一了”。这就是今天所谓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或有人说的白左道路。或者用刘仲敬的术语说,就是从基督教文明,走向费拉主义。
所以在1950年代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跟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一样,甚至跟当时西方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也一样,他们热情地盼望,甚至你也可以说是蛮真诚的相信,一个没有基督的地上乐园。吴耀宗已经不再是古典意义上的(或历史意义上的)基督徒,而是一个费拉。他已经被一种时代精神全面裹挟。事实上,他已经跪下来,崇拜这种时代精神。到底耶稣是大救星呢,毛泽东是大救星呢?到底十字架是道路呢,还是社会主义是道路呢?谁可以解决我们的饥饿,解决我们的社会不公,解决这100多年的落后和整个民族的自卑,到底谁可以叫我们扬眉吐气?四十多万基督徒作出了他们的选择,他们不相信这一切的答案是基督。
所以,王明道称他们是“不信派”。因为他们的信仰已堕落到了一个他们“真诚的”认为,就像同时期在拉美出现的解放神学一样——真心相信一个社会革命和社会改造的道路,能够为中国社会带来希望。这个信念及其压力,彻底影响到他们的策略选择,影响到了他们对教会主权的放弃。因此反过来说,在1950年代,教会的与时俱进的政治理想和政治抱负,重新改写了他们古旧的宗教观;而不是他们的宗教观反过来决定了他们的政治观。
杨:你讲的是一个梳理,但王明道称那些人是不信,不意味着那些人的确是不信。或都是出于真诚的拥抱社会主义运动或共产主义运动。因为确实是在国际上,从192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主流教会的自由派神学。其实我更喜欢把自由派译成“开放派”,它对于这种“此世的天堂”持一种开放的态度,拥抱的态度。
王:我们在神学上,可以说这是一种过度实现的末世论,也就是强烈地期待在末日的终点之前,信仰可以非常强烈地带来整个社会在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改变,直到达到某一个美好的黄金时代。对今生来说,这的确是一种更开放的态度。但对末世来说,这却是一种更封闭的态度。因为它等于向着一个超自然的未来,捂起耳朵,关闭了容许上帝降临或介入的窗户。
杨:是的,基本在西方,20年代以后,我觉得有三种不同的神学路线,在与现代的政权、现代的社会运动的关系上,一种是开放派的,就是拥抱社会运动,用这种社会变革的方式,在此世实现天堂。另外就是基要派的,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天国和天堂都不在这个世界上的。实际上到了5、60年代,更明确的有第三派,也就是所谓福音派。在开放派与基要派之间。福音派并不是完全拒绝社会运动,对社会运动有批评,但同时是积极的态度。他们的参与是一种批判式的参与,在参与过程中把福音传开。福音派在很多神学立场上和基要派是一致的,但在社会参与上又接近于开放派。
王:是的。从全球的教会形态来看,20世纪中叶的中国家庭教会,是在基要派与自由派(开放派)的殊死争斗中产生的,也可以说是在福音派的缺席中诞生的。我在一篇文章中分析到这三种态度。如果说,19世纪是一个宗派大爆炸的世纪,新宗派的不断产生是这个世纪最突出的特征。那么,20世纪的特征,虽然宗派总量还在继续增加,不断细分。但教会最重要的特征,已不再是宗派差异,而是跨宗派的“基要派”与“自由派”之分。也就是说,几乎在一切宗派中,都同时出现了基要派和自由派。譬如,你不能简单的说,长老会是基要派,浸信会是自由派。因为长老会中,既有最保守的基要派,也有最开放的自由派。而浸信会中也是如此。
而中国教会的50年代,完全与西方隔绝。因此我们只看到自由派与基要派的针锋相对。当时中国没有福音派教会,既没有这种神学立场的产生,也没有它可以产生的社会政治背景。在我看来,上帝在那个时代使用了王明道,今天我们去评估他的神学,是非常的基要派,甚至带着强烈的道德主义色彩。如家庭教会的一句谚语说,“王明道讲道德,贾玉铭讲道理,倪柝声讲道路”。但我们这样反思,不是要在今天反过去批评他。因为在那个时代,已经不剩下丝毫的社会空间可以去考虑一个更广泛的福音与文化的关系。因为福音与帝国的关系,已经白热化到了生与死的抉择。上帝在那个时代,恰恰使用了王明道这样的基要派人士。特别的是,他本人又是自立运动的代表。当初政务院召开一个很重要的清算教会的会议,就是处理所谓领取外国津贴的中国教会的会议。这个会是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主持,代表政务院讲话的。他当时是周恩来之下,主管宗教工作的第二把手。习仲勋的手上,是沾了殉道者的血的。当时那些大宗派都很害怕,因为它们之前的确都与西方教会都密切关系。49年之后,这变成了中国教会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原罪。但王明道恰恰没有这个“原罪”。所以他坚决不出席这个会。连最本色化的倪柝声和敬奠瀛都去了。他敢不去。因为他说,我早就跟西方差会没有任何关系了,我是最地道的中国教会。所以上帝使用他的这几个不同身份,神学上的基要派,教会论上的独立堂会,使他成为中国家庭教会可以坚守基要信仰的一个力量。
我补充一点,你刚才说到策略上的考量。还有一种,就是很多家庭教会的老前辈,今天也会常常谈到的,包括一些三自人士也会谈到的,就是当初加入三自的一群人,其实包括了教会很尊重的一群人。如贾玉铭、杨绍唐等,有一种“忍辱负重”的心态和策略选择。他们的确不是基于那种左派的热情,跟吴耀宗他们不一样。但他们也无法走到福音派立场去。实际上他们很难从福音信仰去真实的理解,到底现在发生了什么?共产党进城之后,与我的信仰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甚至去试图理解共产主义的实质是什么?属灵的人能参透万事,但他们缺乏这种从信仰去洞察社会政治格局的一种属灵的敏锐和观察力。因此他们是在一种糊涂和无知中,你可以说是出于政治上的幼稚——但当时谁不幼稚呢,中国所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都是幼稚的,包括储安平都一样,你没有办法看透这个国家,看透这个政权,这一套东西的邪恶实质。因此在他们的心态里,的确就说我在“忍辱负重”,好为教会留出路,留空间。结果呢,不但教会的生存空间没了,连自己的属灵生命都轰然坍塌。
最典型的例子,是我提到内地会宣教士关于中国教会的一本传记叫《中国教会三巨人》,其中杨绍唐、王明道和倪柝声并列。我们通常也会说是王明道、宋尚节和倪柝声,或者说王明道、贾玉铭和倪柝声。转来转去,这几位就是当年教会最重要的人物。而这几个人里,杨绍唐、贾玉铭都成了三自副主席,包括倪柝声也已决定加入三自。他后来退出来,可是退出来也不行,退出来也要抓你。贾玉铭呢,他本是坚决不加入三自的。但他太想保住灵修学院了,这时上海宗教处的官员跟他谈话,也给了口头承诺,他最后就同意了。可是后来他发现,义人的根基一旦毁坏,还能做什么呢。你根本没有办法在妥协之后保住你想保住的东西。几年后,文革还没开始,灵修学院就解散了。
近年来网上有篇流传很广的回忆录,是贾玉铭的一个学生写的。描绘了贾玉铭晚年整个信仰、灵性的崩溃。他后来遇到一个学生,说请你为我祷告。学生说,贾老师,是你教我们祷告的啊。他说,我已经很久没有祷告了,我完全没有力量祷告了。我在主的面前完全没有勇气开口。一代属灵巨人,晚年在灵命上落魄如斯,这是和吴耀宗不同类型的悲剧。因为策略选择的背后,还是信心在权势面前的匮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