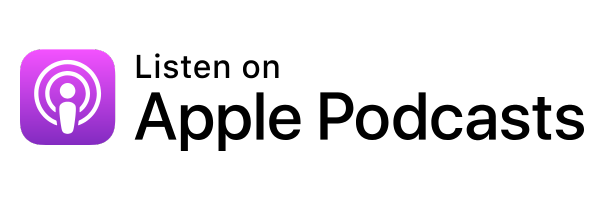4082003 年的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疫情,曾演变为一次突发的公共管理危机。公共危机往往会使宪政制度转型的冲突、方向和缺口,以非常态的方式被放大,提供难得的制度分析的切片。对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作为,从保障信息公开到发挥公共财政作用,当时有不少论述。但在一种传统中央集权制的公共行政思路下,“政府”作为一个与民间相对应的公共行政机构,往往被论者简化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甚至被简单等同于“中央政府”。政府结构的复杂性和各级地方政府在责权上的分立,包括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单一制共和国内,不同地方在突发危机中凸现出的巨大的分殊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忽略了。政府或者被假想为一个单独的巨人,仍像三十年前中央集权体制的全盛期那样,可以如臂使指、从心所欲的去支配每一个权力末梢。或者尽管已意识到中央与地方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但仍寄望于通过运动式的宣传和意识形态的配合,加上对地方官员在人事与政治责任上的严苛,以达成一种临时性的和混杂的危机处理模式。
与此同时,疫情危机所具有的某种紧迫性和社会恐慌心理,也容易使公众倾向于呼吁和要求一个集中的权力中心来力挽狂澜。在传统社会,这一心理往往指向对某个强权人物的渴望。或在一个技术主义的中央集权制下,指向对“中央政府”的膜拜。一些人文学者在呼吁面对危机时需要社会团结和超越性的社群意识时,也不去区分作为民情的一律与作为危机处理的集权模式的一律409,往往简单的加以混淆,由前者导向后者。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的部分学者,则在一项研究报告中建议:“公开宣布所有疑似病例、确诊病例的费用完全由中央财政承担。这样从根本上杜绝患者、医院和地方政府由于经济上的顾虑和困难而产生的延误,确保最快切断每一例可能的传染源”411。假如这一场传染病疫情发生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改革及中央与地方实行财政包干制之前,这个要求应是顺理成章的。中央政府在一种高度集权的财政体制下,几乎垄断了对一切公共财源的支配权,也垄断着对地方政府在人事和财政上的完整的控制权。
中央也在计划体制和单位体制下以财政的方式承担着几乎一切劳动人员的生老病死。甚至国家权力中枢也高度垄断着对于多元利益冲突的某种说服力。因此在一次公共管理危机中,不管纵向和横向的实际利益冲突如何严重,也只是一个行政权力内部的整合问题。公众可以不理会这些内部的冲突,直接要求唯一的和最高的责任承担者和公共资源的垄断者站出来,去承担包括医疗费用在内的一切费用。
1、财政分权与地方主义 自 20 世纪 80 年代的财政包干体制改革,以及全面向地方放权让利的经济改革以来,一个财政上的单一的中央集权体制已经不复存在了。西方学者对财政包干体制通常持有正面的评价,认为其导致了一种中国式的财政联邦制格局,使中央政府的权力(非政治性的权力)大大削弱并有力的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413。
地方与中央在财政收入上分开。收入上的划分必然带来政府支出义务的划分。地方相对独立的享有对地方赋税的支配力,也就以相对独立的责任主体地位,向该地区的民众承担了相当一部分政府职能和政治责任。但是,目前地方与中央在财政收入上的分权是十分清晰的,在财政支付上的责权划分却长期存在着相当的模糊性。这是一种极不寻常的情形。美国经济学家 Roy.Bahl 曾指出这是发展中国家财政分权改革中一个常见的本末倒置现象。从理论上说,应当由事权来决定财权,中央政府首先必须确定地方的支出责任,才可能反过来达成对税收收入的合理分配。但是Bahl 分析说,“支出责任的划分更多地涉及到政治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将使行政性的财政分权向着政治性的地方自治转变,如要求中央权力放弃对地方大员的人事控制权416。
另外,随着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极度不平衡,地方财政的贫富也日渐悬殊。尽管中央财政的转移支付对地区财政平衡能起到适度的调节作用。但中央财政的职能,显然不能、也不应该在根本上让富裕地区的人群与贫困地区的人群去享受一个平均的公共服务水平。在地方政府的财政能力出现明显差异的情形下,地方政府对于本地区社会财富的剩余索取权,就与其向本地区利益负责的财政责任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地方的分殊利益在一个非集权式的经济和财政体制下便开始凸现出来。这种趋势和夫妻共有财产制是类似的。在大部分夫妻双方收入比较平衡的时代可能相安无事,但在收入高度悬殊的时代就会向着夫妻双方的分别财产制演变。某种在传统的中央集权制的思路下,要求地方从全局和意识形态的高度出发,付出地区利益而无补偿的做法,就开始受到来自地方越来越大的拦阻。而中央与地方之间,一些非制度化的政策谈判模式和惯例也在形成当中。两个突出例子是 90 年代末期国务院将部委系统的社会保障移交地方的决定,及 1998 年大洪水之后强迫长江上游省份退耕还林的决定。
地方独立财政的确立,尽管事实上得到了中央政府适度的默认419。而突发事件和公共行政危机之于宪政转型的意义,在于地区利益的主张,可能因为某种危机的凸现而增强正当性,使地区之间及地区和中央之间的财政冲突获得谈论和妥协的机会,从而促使制度的良性变迁。
2、外部性
在讨论公共行政的方向和模式时,哈丁提出的“公有地悲剧”和奥尔森对于“集体行动逻辑”的分析,是两个很著名的模型。这两个理论都可在科斯定理下用“外部性(externality)”的概念加以解释。公有地因为产权的开放使得任何人的放牧都是无成本的,这是成本外溢的外部性,刺激牧人的放牧行为,造成过度无节制的放牧。而在奥尔森分析的集体行动逻辑中,如果一个人不会被排除在一种集体物品所产生的收益之外,他就不会积极的去参与集体物品的供给。这是收益外溢的外部性。造成人们常说的搭便车行为。科斯指出产权界定的衡量标准,就是看怎么样才能最大程度的消除外部性。外部性是不可能彻底消失的,但一般来说,只要产权界定清晰,就足以克服一项行为的外部性,防止上述两种情形下因外部性而产生的无效率状态。另外有些事情是必然存在外部性的,完全不可能通过私有产权的界定去消除。如维护生态环境和交通顺畅。这类事物或条件被称之为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公共物品因为存在着不可消除的外部性,不可能通过私法的保障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因此应由政府来提供。
进一步的问题是,当“政府”不是一个整体性的单一概念时,各种公共物品到底该由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来提供更好呢?在联邦制国家和原单一制国家的财政分权改革中,“外部性”也是判断中央(联邦)与地方政府财政责任划分的一个有效的概念。通常认为,收益或成本外溢程度较高的事业,应由中央财政负担,比如军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汉密尔顿曾经在联邦主义的思路下,详细论述过为什么军事(共同防务)必须由联邦来提供的理由421。也可以用哈耶克关于“知识分立”的概念来解释为什么地方政府能够提供比中央政府更好的行政服务,并更容易受到监督。在单一的中央财政下,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一个面积广大的花圃,中央政府就像花圃中心的喷泉,不管如何均匀的转动,受益最大的始终是喷泉周围的那一块地(首都),越是离权力中枢远的地方,受益就将越少。同时这也养成了接近权力中枢的周围地区对于中央财政的依附性。加上行政系统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中央财政的职能越大,地方对于中央财政的敲诈和欺骗就越厉害。
财政问题和赋税问题一样,影响着立宪政体的塑造和变迁。
3、SARS 的外部性问题
要求政府负担 SARS 病人一切医疗费用的观点,认为 SARS 因为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因此是一种外部性极强的疾病。即是说它的危险和代价并不由感染者独自承担,而是由与感染者生活在一起的整个人群集体承当的。而感染者对此一般并无过错。因此害怕感染的人群应该向感染者购买这种防止感染的权利。即由政府花钱把感染者隔离起来并且进行治疗。张五常撰文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患病不构成一种可以配置的权利,不能拿来与烟囱的污染相类比。因为没有人会在权利界定清晰的情形下愿意患病,患病者和周围人群都将为此病付出可能是生命的代价。权利的界定对外部性的消除是没有意义的。所以“向感染者购买防止感染的权利”的说法不能成立422。张认为,SARS 的确具有外部性,但不能以科斯定理来推论。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政府为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向感染者购买他(她)与生俱有的一种权利,即人身自由。我同意这种看法,因此尽管《传染病防治法》没有规定对传染病人的强制隔离应该给予补偿,但对无过错的感染者的人身限制,的确已构成了政府给予被限制者的补偿责任。
但强制治疗和强制隔离又有不同,后者针对和侵犯了病人的人身自由,所以应该补偿。但前者却维护了病人的生命权。就算病人本不愿治疗,这也属于民法上的无因管理行为。应由受益者即本人承担治疗费用。尽管社会公众也从一个病人的康复中间接获益了。但这最多只能产生政府在病人无力承担医疗费用时的补助义务,并不能因此豁免感染者的自我支付义务。因此属于政府职能范围的只能是因强制隔离带来的补偿责任,和对于无承受能力的患者基于一般社会福利原则的经济补助义务。要求政府负担一切 SARS 病人的所有治疗费用,出发点固然好,但却是不恰当的夸大了政府在社会中的角色。在财政上将政府设想为一个上帝,这和在政治哲学上将国家放在至高者的位置上一样危险。希望利用政府来解决一切问题,担负一切责任,也就是希望政府享有无限的权力。而对于政府财政支付职能的任意扩大,也就是对于政府财政收入权限的相应扩大。这种要求忽略了社会在解决医疗负担这个经济问题上存在着政府财政以外的诸多途径,个人的自我负担和家庭融资,保险业的商业化分担,社会保险基金的运作乃至慈善捐赠424。
4、SARS 疫区的外部性问题
即便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对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有财政责任。那么应由地方政府负担还是中央政府负担呢?如前述中央与地方在某种“财政联邦制”模式下并未清楚界定财政支付的责权范围,而《传染病防治法》也没有针对传染病防治的财政责任进行规定。以 4 月 20 日卫生部副部长高强的新闻发布会为界,SARS 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的真实情形被披露。各地正式进入对突发公共卫生危机的防治和处理。但在近半个月的时间内,各级政府在财政责任上的反应不一,所确定的责任范围也大相径庭,可以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卫生部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表示《传染病防治法》并未规定政府应当支付传染病的治疗费用,政府只能对无力承担者进行补助。财政部 4 月23日公布成立 20 亿非典防止基金,除了用于医疗设备和条件的改善以及提供医疗人员的补贴外,其用途之一也仅仅是“对无力承担医疗费用的病人进行医疗救助”427。
有论者提出由中央财政负担医疗费用的一个理由,就是时间紧迫。认为“中央政府可以在最短时间内作出可信的承诺,而地方比较迟缓”429,反倒是北京市和湖北省政府作出了力度上最接近的承诺。原因就在于地方的分殊利益造成了制度选择上的不同偏好,而利益的偏好往往比普遍利益更靠得住。
强调在突发事件中的地方财政分权,一个基本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假设,就是不会有人会比自己更关心自身的利益。名义上代表全国整体利益的中央政府,是否会比北京市或湖北省更关心当地的疫情?中央财政负担说和一切推崇中央集权体制的理论,其实都建立在一个对此肯定作答的前提之上。SARS 的传染性意味着病人与非病人之间的外部性关系,据前述分析这是要求政府承担部分财政责任的根据。但这里还存在另一个外部性问题,即疫区和非疫区之间的外部性关系。由于SARS 的爆发和传播就全国而言仍然是地区性的,绝大部分病人集中在如北京和广东等个别省份。而传染性或者外部性是必然会随着地域的扩大而减低的。也就是说SARS 病人对于北京人群的安全所具有的危险性,和对于一个非疫区或疫情极度轻微的地区人群的危险性,是有天壤之别的。对于政府财政负担甚至中央财政负担的迫切要求也可能大相径庭。事实上许多省份只需要严格检疫外来人员,甚至为了本地民众的利益对外地尤其是来自疫区的人员采取扩大化的、甚至是一刀切的强制隔离措施,就基本上可以免除危险。这些省份对采取类似的行政措施的迫切要求,显然大大高于对中央财政负担的需求。因此中央财政负担只是一个让极少数疫区严重省份受益的公共政策。这少数几个省份(尤其是北京和广东)恰好又是财政力量最雄厚的地方之一。在此情形下不积极诉诸对地方财政的要求,反而一昧呼吁中央财政。既是一项极不公平也注定并无效率的舆论,也是一种被中央财政和中央集权制的传统所误导的思维迷误。
其实,出于对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关注,北京市政府愿意由财政负担医疗费用的需求,也大大超过中央政府。寻求疫区政府的财政承诺,比寻求中央财政的承诺更有效也更及时。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涉及到外部性的另一个问题。即外溢的收益如果是一种并非排他性的收益,且这种外溢不会影响相关人群的预期的既得利益,那么收益的外溢就不会对相关人的行为选择构成外部性的影响。比如女士们不会因为使用香水会被他人闻到,从而减少香水的消费或选择搭便车去闻别人的香水。SARS 的防治也是一样,北京市不可能因为防治工作会间接对其它省份有利因而降低防治的投入。因为 SARS 疫情对北京本土的即时的安全威胁,数十倍的高于其它省份,防治工作所预防的风险和带来的收益是如此巨大而必不可少,其它省份会不会因此获益,不会对北京市财政负担的决策构成任何消极影响。
对那些只有极少数甚至完全没有 SARS 病人的省份而言,地方财政的支付能力绰绰有余,完全不需要中央财政出面负担一切治疗费用。而对那些疫情严重的地区而言,地方政府负担治疗费用的利益驱动也数十倍的高于中央政府。就疫区和非疫区的关系而言,SARS 防治工作不存在严重的外部性问题,而非要由中央财政出面承担一切治疗费用不可。同时更要区分一点,防与治是两个方面,防的工作对非疫区而言具有相对较高的收益的外部性,而“治”的工作针对非疫区而言收益的外部性是很微弱的。因此中央财政的有限拔款把重点放在“防”上而不是放在对医疗费用的负担上,其实是较为合理的财政划分。相比之下,真正具有较高外部性而需要中央政府出面的,不是治疗费用问题,而是地区之间的隔离措施。
5、隔离:外部性与行政目标的差异
地区间的各种隔离和预防措施,具有极高的外部性。疫情最严重的地区,为保障其它地区的人群安全,最需要采取与外界的隔离措施。但疫情最严重的地区,恰恰最缺乏采取对外隔离措施的利益驱动。因为这是一项收益完全外溢的行为,譬如北京市如果宣布封锁,禁止市民外出。隔离的成本和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各方面的损失都将由北京市独力承担,但巨大的收益则是由所有非疫区人群共享的。因此除非大多数省份愿意一起为北京市提供补偿,或者直接呼吁中央政府出面宣布封锁北京市的对外交通,才可能解决这个因外部性带来的地区间的利益冲突问题。否则即使疫情更为严重,北京政府也不太可能主动采取对己不利的措施。即使在学界,人们只听见北京的学者们频频提出要求由中央财政负担医疗费用,然而尽管几乎所有省份都希望北京市能主动把自己封锁起来,人们却听不到北京的学者们建议北京市采取对外隔离措施430。
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北京为首都,中央政府与北京市存在着极大程度的利益重叠。因此中央政府、北京政府和其它省政府之间在隔离措施问题上,出现了比财政负担问题更尖锐的利益冲突和行政目标的差异。除了北京市因为利益的外部性问题而不愿支付被隔离的代价外,中央政府出于与北京的重叠利益,以及涉及全局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甚至会比北京市政府更不愿意隔离。但这些顾虑对大多数省份来说却并不重要。因此尽管“万众一心”的防治非典工作如火如荼,人们却看到在行政管理和公共危机处理上非常无效率的一幕:由全国各省、各市去严防死守,监控、隔离、甄别、检疫和制止外来人员,而不是由极少数疫情的重灾区主动隔离和限制人员外出。这就和科斯讨论的工厂烟囱的例子非常相似了。不是大家凑钱给烟囱买一个净化器,而是大家一人一个净化器431。仅从经济效率看,地方财政可能累计为此多花掉了几十倍的钱。
卫生部在 4 月 8 日颁布通知,“将传染性非典型肺炎(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征)列入法定管理传染病”。我国《传染病防治法》明确将传染病分类为甲、乙、丙三类。并规定卫生部可以决定后两类的新增传染病病种,国务院可以决定新增甲类传染病(目前只有鼠疫和霍乱两种)的病种。但卫生部这个通知只字不提 SRAS 传染病属于哪一级传染病。只在规定可采取的控制措施时说“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第二十四条(一)款执行”。这一条款是“对甲类传染病病人和病原携带者,乙类传染病中的艾滋病病人、炭疽中的肺炭疽病人,予以隔离治疗”。从卫生部的权限看,SARS 的定级是乙类传染病,但事实上 SARS 的传染性远远超过艾滋病和肺炭疽,而达到了甲类传染病的程度。同时,尽管《防治法》规定经市一级政府决定,可以宣布疫区,并可依法采取各种强制措施。但疫情极端严重的地区如北京市,从未正式宣布为疫区。很多省份都曾对某些地段采取了事实上的封锁措施,对SARS 病人和疑似病人之外的人群也采取了强制性的隔离。但《防治法》规定只有甲类传染病才能经省一级政府决定封锁疫区。而只有依法封锁疫区,政府才有权将对人身自由的限制从传染病人扩大到一般人群。但因为国务院并未明确将 SARS 列为甲类传染病,因此一切封锁措施和针对疑似病人及普通人群的强制隔离措施毫无疑问都侵犯了公民的宪法权利。
在疫情中,绝大多数省份均颁布过防治条例或政府通告。其中大多数省份都对来自疫情严重省份的人进行强制性的身体检查、健康情况登记,或对与病人有过较深接触的人进行强制性的观察或隔离。也有少数一些省份对来自严重疫情地区的人进行一刀切的强制隔离。其中长春市在 5 月 2 号发布的公告,采取的隔离措施是最严格的。其隔离范围也扩大到极点:一切由外埠返长的市民及与其有过接触的人员,必须在家中强制隔离 14 天,一切 4 月 18 日之后抵长的外埠人员,必须在指定宾馆强制隔离 14 天432。这些严重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极端措施,和平常情形下政府侵犯公民权利的一些案例不同。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疫区和非疫区之间、以及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在行政目标和分殊利益上的严重冲突所致。使一些地区在恐慌中不得不选择极端手段以求自保。一方面因为危机的急迫性,一方面因为中央政府在外部性最强、最需要超越地区利益去行使职能的事项上,却出于自身利益的衡量而陷入无能。因为不愿将 SARS 明确列为甲类传染病,更不愿在疫区采取封锁和交通隔离等措施。地方的各种大胆举措在中央集权制的主动退却下获得了一种临时性的被容忍的“政治正确性”。以至中央对这些举措均网开一面。于是相当一个阶段内,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已构成了对于一般人群宪法权利的大规模侵犯。假设疫情不幸继续扩展,一些地区也许还有更极端的措施出台。而中央集权制下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矛盾也可能尖锐到难以敷衍的程度。
SRAS 事件因此为思考中央与地方的制度转型、甚至为思考整个宪政转型的模式提供了难得的例证。在今后类似的各种公共危机中,一个常设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尤其是一个可以直接代表各省平等利益的议院模式(参议院)的缺席,可能使危机下的地域冲突除了转化为政治问题之外,无法期望获得一个技术性的出路。一个非常设的全国人大,不可能在类似的突发危机和地方冲突中出面对政府的公共行政选择构成制约和审视,并提供谈判桌,或充当地方利益冲突的调停人和仲裁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在公共危机中强行出面,则可能造成和积累公众和地方对它的合法性的质疑,并转化为对常设议会的制度需求。
注释:
此处作了修订。
代的某种向往和回归。
http://www.sxet.com.cn/ecolook/mrjj.asp?newsid=5285。
411 《让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成为尊重生命的国度》,杨支柱、秦晖等。http://www.wtyzy.net。
政治研究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413 Robert ·D· Ebel《财政分权和公共支出管理》,世界银行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cn。
414 参考注 8。
415 Roy Bahl《财政分权制的实施原则》,世界银行网站 http://www.worldbank.org.cn/
政策的成本。
可能。
政分权制的实施原则》,世界银行网站 http://www.worldbank.org.cn/。
度设想的推动力上。
的平衡。
421罗伊·巴尔《财政分权》,同上。
422 张五常《从高斯定律看瘟疫市场》,宪政论衡网站,www.xianzheng.net
423 2003 年 4 月 24 日《北京市地方税务局关于对防治非典型肺炎捐赠有关所得税问题的通知》,规定对捐赠现金和财物给予所有税计税扣除,以鼓励捐赠。
424 当时在北京天则经济所的讨论会上,著名维权人士王海曾作了《建议人大授权政府为所有“非典”患者买单》的发言。茅于轼在评论中指出,第一,如果一个百万富翁的患者也要政府以税收来负担,是让人难以接受的。第二,由中央财政负担,不提地方政府的责任,是否合理也还需要讨论。这是笔者所见在当时几乎唯一对类似观点公开提出质疑的。即使是在自由主义学者中,多数人在公共危机中也会不自觉的回归于中央集权制的思维范式。http://www.unirule.org.cn/。
http://www.southcn.com/news/china/zgkx/200304231069.htm
426《关于非典型肺炎患者医疗费用有关问题的通知》,新法规速递,http://www.law-lib.com/
工作的通告》,同上。
428 参见笔者与秋风的讨论,《关于中央财政负担再回秋风》,宪政论衡网站,www.xianzheng.net。
地方财政自行负担执行政策的成本。
430 在京学者据我所知,只有中国政法大学学者萧瀚一人曾提出北京市应当实行“戒严”,以防治疫情对外扩散。
431 参见科斯《社会成本问题》,《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5 年,P3。
http://www.law-lib.com。
2006 年初于成都大学。
2011 年 10 月完成修订。
——摘自《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