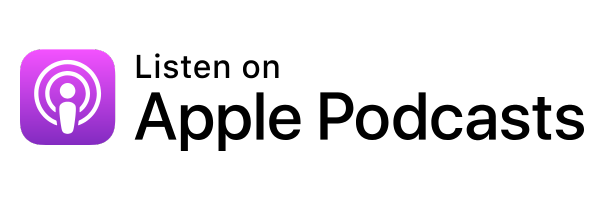2007 年,获得艾美奖 6 项大奖的美国剧集《迷失》(Lost)播到了第三季。全世界大概数千万人和我一样,或出或入,或吃或喝,等着这个故事漫无止境地铺陈下去。我的表达略显夸张,我对这部剧集的爱慕如司马昭之心。人们牵挂一部漫长的韩剧,也许是牵挂一份曾经失丧或正在失丧的爱情,牵挂那些生命里的饶恕与成全。而我牵挂剧中的那个南太平洋小岛,却是牵挂那些坠机之后的灵魂。他们身体已经得救,灵魂还在海滩与丛林间漂流。灵魂就是灵魂,即使出自虚构的人物。虚构依然是位格之间的交流和牵引,编剧、导演和演员,无数人的位格在一个虚构人物中延展。当我们说虚构文本反而更显真实,是指那个被延展出来的位格内涵,只可能出于一个有位格的存在。被延展出来的理性、忧伤和幸福,就是真实本身。艺术的真实性也是一个位格议题。一个角色,不过是对一种位格内涵的比喻。屏幕或小说里的一个名字,不过是一个或几个位格者的化名,仿佛一个 ID。所谓艺术性,就是位格内涵的真实性,使一个虚构人物的结局与我们息息相关。使我牵挂剧中的杰克,竟像牵挂我的一个朋友。
就如剧中的幸存者们终于进入那扇神秘的地下舱门,被说服每隔 180 分钟就必须将一组数字输入电脑,否则世界将会毁灭。洛克深信这就是他们坠机到此的使命。他问那些不信者,你怎么知道这不是在拯救全世界呢?如我们坐在电视机前,你怎么知道这部电视剧真的与你的灵魂无关?就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说,“你这作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作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一切并非尽在掌握,那么小说、电影、足球、音乐,乃至哲学、历史、法律与政治,所有人类文化,一切位格者相交的产物,至高者岂会在里面没有他的旨意,这宇宙的王岂会割出一块来“一国两制”。如果救赎不是可以自己赚取的,救赎就意味着对上帝至高主权的信服。耶稣说过一句很精彩的话来表达这位公义者随己意的恩典。他对犹太人说,“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
有人说到进化论在证据上的不足,或在科学上与信仰冲突。其实对我来说,人是否猴子变的,离信或不信都很遥远。神难道不能从猴子里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造物主可以将一切人能发现的规律和机制,放在它该在的地方。一切科学假设,或被推翻或被姑且同意,只不过是对现象的归纳。科学的最高描述方式就是一种自然主义的表达。今天你发现万物都有引力,有就是有。明天若发现也不一定,不一定就不一定。人在理性上可以姑且接受一个科学假设,作为理解物理世界的工具。但自然科学永远没有一个方法,可以有效地质疑上帝的主权。从逻辑上说,反而只在一种情况下,似乎能够怀疑上帝的存在,就是科学家们简直找不到任何规律。有的东西会掉在地上,有的不会;有时候会,有时候不会。如此你才能说,就人类智力所及,一切都好像出于偶然。看起来这世界不像有上帝的样子。或者曾经有,但那位神圣者显然已从一切事物中撤离,所有的规律都开始失灵了。
即使这样,也不太能质疑上帝的存在,反而质疑人在受造物中的位置。因为最大的一种可能,是上帝没有将足够理解这个世界的智慧和理性放在人里面。就像没有放在一切动植物里面一样。对一只狗来说,上帝的确不存在,世界也没有规律。所以对牛弹琴,等于让一只狗看《迷失》。看不看,这个世界都是偶然的。人若也认定世界是偶然的,倒是和一切动物的世界观相一致。
神迹和神迹的缺乏,是上帝显明他自己的两种方式。就像公义与不义,也是我们看见一个审判者存在的两种处境。当我们不能不痛恨一切不公不义,是谁在我们心里放有一个“公义”的影子。我们对外的“否定”,恰恰出自我们对心中道德律的肯定。什么是神迹,如果神将一种进化的机制放在受造物中,从猴子中兴起人来。这是神迹。如果神各从其类,在一天中创造亚当,并将子孙的繁殖放在亚当夏娃里面。这也是神迹。如果神透过男女身体的结合,叫生命无中生有,以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的机制进化出来。这是神迹。如果神透过玛丽亚的身体,由圣灵感孕,把道成肉身的基督放在里面。这也是神迹。对基督徒来说,一个有规律的世界是向着永恒敞开的,生命也向他的造物主敞开。每一件事都可能没有发生过,但每一件事都有可能发生。我不相信进化论,不因为这个假设有许多漏洞,也不因为这个机制能够挑战上帝的主权。只因为我相信《圣经》是上帝进入历史,并透过以色列人所记载的启示。太多的奥秘或许我不明白,但上帝如此启示,我就如此相信。因为神的启示高过人的理性,因为幸福就是委身于一种信心,而不是在信心的外面掂量一辈子。
这样看世界,或这样看《迷失》,那么每一秒钟都有盼望,都有托尔金的“魔法”。上帝可以预备任何一个故事,来使你感动。就像他可以借着全世界最笨拙的一张嘴,叫一个人悔改信主。因为这是他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我们只是客旅,是寄居的。当人忘了这身份,活得如鸠占鹊巢,就会有一些痛苦不期而遇,帮助我们重新审视与这世界的关系。
于是我看见一架从悉尼飞往洛杉矶的航班,偏离航道一千公里,机身折断,坠落在小岛的海滩上。40 多位幸存者中,一个妻子坚信自己被抛出机尾的丈夫还活着。其他人以为她需要心理医生,但她知道自己需要的是信心。到了第二季,她丈夫终于从岛的另一头走来,信心的来源也有了交代。原来坠机之后,她的末期癌症奇异地消失了。这个岛似乎被一种神秘的力量簇拥着,到处都有地下船舱,仿佛大海中不动的挪亚方舟。这一群人,怀着各自的罪过和愁苦,从这个世界中被分别出来。一场灾难带来了一场拯救。这就是《迷失》胜过一般电视剧集的魅力。这不是一座坠落的岛,而是一座医治的岛。导演将每个人坠机前的一生,与坠机后的改变穿插讲述,使“劫后重生”这四个字变得名副其实。犹太人尼哥底母曾经问耶稣,“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导演的回答是,让一群人从三万英尺的高天坠落,在必死的处境中被挽回,然后用 5、6 年的时间,向观众一一见证他们如何从捆绑中得释放,从苦难中得安慰。
可恶这个故事还要几年才能看得完。长篇电视剧可能是杀死时间的,但难得像这部剧集,它的漫长反而增添了位格相交的真实性。回想我自己的拯救故事,或我对一个朋友长达十年的观察。5、6 年实在也不算长。只是你需要问,我有这个感动,要委身于这个故事吗。
《迷失》会打动很多不甘心迷失的人。若你认定世界是出乎偶然的,剧中的外科医生杰克会成为你的偶像。这是一个近乎“花无缺”的家伙,任何危机所需的勇敢、温柔和利他主义的爱,杰克应有尽有。如果他没有坠机,会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楷模和稀缺资源。但杰克并没有成为所有人的拯救。杰克的人生甚至和杀人犯索伊尔一样沉重。父亲的死在他心里留下的,足以使他的余生成为一场苦役——幸好他坠机在这个岛上。他没法救自己的灵魂,也没法在岛上组建一个共和国,更不可能使癌症消失,瘸子行走,叫哑巴开口,死人复活。
当来自世界的营救希望破灭后,这些和我们一样有灵的活人,开始被这个岛拯救。洛克下肢瘫痪,却一直希望去澳洲实践野外求生的梦想。他被拒绝后,坐着轮椅上了飞机。在惊心动魄的坠机现场,洛克从海滩站起来,开始奔跑。谢谢ABC 花了 500 万美元来拍第一集的坠机现场,万事相互效力,只为这一个镜头就已值回了代价。
这个无名岛的魅力,在于叫所有人的命运都牵连在了一起,甚至包括观众。就如英国牧师和诗人约翰·邓恩那一段著名的布道辞,“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孕含在人类之中,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敲响”。诗人艾略特和布洛茨基的推崇都没能使邓恩出名,但这段话因为被海明威引用,在被拿掉信仰背景之后,就成为近一个世纪以来最流行的人文主义语录。有趣的是在第二季,竟有一段洛克与他的俘虏关于海明威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对话。那位被俘虏的神秘岛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自己的才华是一种恩赐,并为这种恩赐而活。但海明威却终身劳苦,活在自身天才的阴影之下。他问洛克,你是哪一种呢?
洛克的全名是约翰·洛克,这种借用也颇有意味。这部剧集中还借用了另一些启蒙时代以来的显赫名字,如雨果、狄更斯等。曾有四个人先后被指证为“美国之父”,第一个华盛顿是政权意义上的国父;第二个麦迪逊是政体意义上的宪法之父;第三个洛克,他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民主之父;第四个加尔文,则是宗教意义上的信仰之父。洛克的民主与契约理论,在四个人中是承上启下的一个,通过政治的盟约,将一个上帝之城降落在一个世界之城。就像这些流落小岛上的人们,日子一长,他们彼此对生存意义的分歧,也开始在这两个城之间摇摆了。
第二季故事的重心,不再是杰克的人性乌托邦,而是洛克的信仰及其动摇。他和黑人牧师艾克发现了另一个地下舱口,有人在这里观察那些每隔 180 分钟就将数字输入电脑的人。洛克的信心遭到致命打击,那个每隔 180 分钟的使命是否一个谎言?既然活了下来,活着为什么。信仰与苦难的意义遇上了一个岔口。一种还是加缪式的盼望,西西弗反复把石头推上山顶是为什么,洛克每隔 180 分钟将那组数字输入电脑就是为什么。世界的意义就是在无意义中坚持,就是在虚无中打捞一个倒影。加谬的意思是,“更加荒诞就是荒诞的敌人”。但艾克的信仰反而被燃烧起来了,世界不可能被高科技拯救,就像不能被杰克拯救一样。电脑前的守望不是拯救本身,却是拯救者对被拯救者的一场测试。“测试”不代表测试是虚假或无意义的,拯救者给我们的每一个角色是否有意义,在于拯救本身,而不在这个角色。上帝若放我在一辈子扫大街的位置。我的使命就是像一个基督徒那样扫大街。脏了又扫,扫了又脏。如果没有上帝,这件事本身有什么意义呢。接受使命就是接受“测试”,这个想法使艾克对这个岛的理解超出了西西弗的模式,也胜过了杰克的沮丧。有些类似于犹太人在一生中严守诫命的模式。不过最终的结局和意义怎样被给出来,使这一诫命模式再次被超越?这也是我对后面故事的期待。一个什么样的盼望,终将被放在一个流行文化的作品里——除了美国,其他地方很难见到这种隐含宗教性盼望的影视作品,只有韩国差不多了。
神秘的丛林,如同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无名小岛也如大海中的眼,又如眼中的瞳人。这个虚构的小岛上有一种力量始终环绕着人们,尽管如今还不知道那是什么。但那力量看顾保护劫难中的余数,“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苦难是化妆的祝福,这是《迷失》的主题,也是 911 之后美国的新教保守主义开始复兴的一种自况。《泰晤士报》的评论说,好莱坞长期宣扬“不信上帝的人文道德主义”,但近年来也重新发现自己的信仰了。《迷失》常提及灵魂的话题,导演艾布拉姆斯解释说,“世界上所有的冲突几乎都与信仰有关,真正成功的影片应当用一种新颖的方式去讲述这些事件。”
我不一定有机会从三万英尺的地方坠落,但我信仰之初,也来自一次约两米高的坠落。2005 年 4 月,在海上第一次决志祷告之前大约半年,我在家中爬上书架,去拿最高一层的书。忽然从梯子上摔下来,后来缝了九针,养了近一个月的伤。当时我一人在家,躺在地上血流不止。一时突破了一年多的理性障碍,我第一次独自开口唱诗,并祷告说,神啊,如果你在,请你在我心里显明。因为《圣经》说没有你的许可,连一只麻雀也不会掉下来。没有你的许可,我也不会从这梯子上落下来。我既落了下来,就不是没有意义的。
这一跌倒是我后半生服罪的开始。叫我看见个人与历史的意义,不是人赋予的,而是上帝给予的意义。这意义叫我不再受到偶然性的威胁。我满墙的书架,仿佛人的理性阶梯。爬上去,意味着人向着他自己的攀援。但我从上面实实在在地摔下来,上帝的话语也实实在在地临到我。就是这句“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我掉下来,内心的骄傲就开始耗散。那时人软弱,软弱使人的肉体变空。肉体一变空,心就能接受光,看见一个高于自己的心意,进入我的历史。
我的坠落,也恰如一次 lost,也是灵魂的一次割礼。一个理性人的血气、傲慢和对二者的无能为力。若不跌倒,我就不能看见,就如洛克不坠机,就不能行走。人与神的距离不会因我们的仰望而消除,只能因为至高者的迁就。就像如今我俯下身来,与三个月的孩子隔着 10 厘米说话。我若不俯身,就无话可说。若没有爱,又何必俯身呢。上帝俯身,因为他不愿放弃我们。从一开始他的计划就是放弃自己,不放弃我们。涂抹罪,不涂抹罪人。罪人的肉体在上帝的永恒旨意中,竟还有蒙保守的价值。这就是割礼的意义。亚伯拉罕的割礼只是象征性地割去身体,作为立约的标志。耶和华神则在燃烧的肉块中经过,象征着十字架上唯一真正的献祭。
那个岛其实不是荒岛,没有神同在的岛才叫荒岛。若只活在一个“如神在”的世界,不如去那个岛。在真实的磨难中,人一辈子停电、熄火、失恋、失业、卖房、负债、离婚、堕胎,或者生老病死。如果所爱之人死在眼前,心爱之物化作乌有。人在人海中犹如孤岛,谁将看顾你,如同看顾眼中的瞳人?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