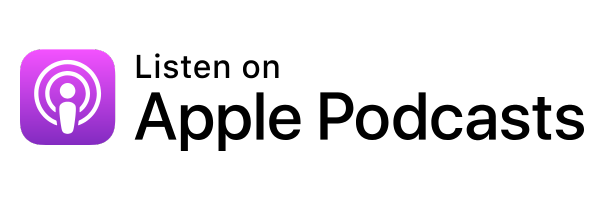我最欣赏的当代诗人是成都的柏桦,他的诗看似没有烟尘,仿佛躲在六朝的最深处,像那首著名的《在清朝》。但他的诗恰恰真实感最强,在一个被贾彰柯闻出来有“兵荒马乱”味道的当代场景中,柏桦写下那些带着亡国气息和挽歌般悲哀的句子。就像普希金在被流放前那一年写下的《乡村》,“在这里,我的年华在幸福和忘怀中,不知不觉流逝”。2007 年,《中国青年报》记者晋永权的书《出三峡记:大迁徙的私人记忆》中,有节制地引用了这句诗,来触摸 16.6 万三峡移民的灵魂。
贾彰柯再次没有令我失望。他说在奉节,看见一个男人当街炒菜,背后是滔滔江水,万丈深谷。那种在生活的边缘像纪念碑一样矗立、又像羔羊一样温顺的气度,打动了他拍摄这部电影。2006 年,我在奉节和云阳新城的新码头,也见过乡民们的这般气度。总有一部分人,会在时代的高歌猛进中沦陷。最直观的是在三峡库区,一座座千年古城在洪水中湮没。不是象泰坦尼克号那样惊声尖叫,而象一块卵石悄无声息。这是一个被拆迁安置的时代,也是一个大洪水的时代,但在电影中,人们低头生活,抬头看见了 UFO。
影片中,贾彰柯的纪实性风格,又天才般地添进超现实元素。两个人来奉节寻找爱人,因为都抬头看见了 UFO,而被勾连成为一部电影。地上的寻找,也指向了举目的仰望。叫我又想起布莱希特,他的戏剧《四川好人》,经过行政区划的一次调整,就成了“重庆好人”。一个山西汾阳的煤矿工人到奉节寻找前妻,政府人员嘲笑这个乡巴佬,说奉节早不属于四川了,现在属于直辖市了。听见这句台词,我的悲哀胜过了奉节城被淹没的那一瞬那。奉节其实消失了两次,一次在文化上被拆迁,一次在物理上被拆迁。一个行政命令,活生生把文化意义上的四川砍为两半,将一个族群从历史的血肉、也就是从彼此位格相交的一个生活世界(living-world)中抽离,在行政区划的地图上完成了对生命的一次拆迁安置。然后另一个行政命令,再次挥斥方遒,就用大洪水将一个城市彻底抹去了。
这时,那个山西矿工来到三峡,寻找他的爱情。民工们拿出钞票,将毛泽东的人头倒转,指着背后夔门和壶口瀑布的图案,介绍自己的家乡。有人说这意味着家乡被金钱化了,其实还是被国有化。当家乡被印在中央银行的钞票上,意味着一个高于城邦之上的国家,征收了每个人的家乡,就像征收每个人的房屋一样。公权力的逻辑是如此显赫,超越在文化的逻辑和生活的逻辑之上。比它更高的公义是什么呢,贾彰柯只给了观众一个幽默但却心酸的回答。他说,一边寻找一边仰望吧,比生活更高的是权力,比权力更高的是 UFO。
在这部电影中,UFO 象征着一种超验的现实。令人寒心的是,这也是一个非道德化的、和数码化的超验现实,就像电影中几乎人人都有的手机,音乐振铃基本上从一开始响到了最后。手机是这样一种事物,它将我们从每一个当下呼召(calling)出来,使我们与他人的位格在一个超时空的幻象中延展。在巴别塔事件后,上帝在整个人类中曾单单呼召了亚伯兰(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大陆第一位基督徒导演甘小二,拍摄了两部农村基督徒题材的影片。他的第二部作品《举自尘土》参加了 2007年的香港电影节。影片里有一位河南乡村牧师,诙谐但略显轻佻地把祷告称之为给上帝打手机。他对信徒说,有事就给上帝打手机,我们的神是永远不关机的,绝不会不在服务区。
手机的普及,给奉节的民工们带来了一种数码式的拯救。每一次 calling,就像一次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超级链接,使我们的位格延展到地极。每一次彩铃响起,就像吞一次鸦片,生活的虚无就被另一种虚无暂时的填满。就像那个崇拜周润发的青年民工,每次点烟都要模仿“许文强”。每次接电话,“浪奔、浪流”的《上海滩》主题曲就响了起来,多么强大的超级链接,又多么方便的呼召。
连奉节城上空的不明飞行物(UFO),也是这种数码式拯救的一个延续。
一座城市的淹没,是一种锥心刺骨的命运。多少一笔勾销的故事,多少公共梦想对个人生活粗暴地撕裂与覆盖。如果没有一部手机,我们怎么跳出现实,去贬低苦难在我们生命中的位置。
那个女护士也在奉节寻找到他的丈夫,却不得不在江边别离。她转身离去,一座移民纪念牌化作火箭,拔地而起。“神六”上天,爱情落地。这是贾彰柯另一个超现实的神来之笔。和从天上来的 UFO 一样,从地上去的火箭也是一种超级链接。“飞天”,也是自古以来一个自我拯救的梦想。不过和钞票一样,“飞天”也只是一个国有化的梦想。卑微的人们举目仰望,火箭和 UFO 同时都离他们太远。他们只有一部手机,死死攥在自己手里。
火箭和通讯卫星,在今天构成了国家主义的一部分。诗人大卫颂赞上帝布满宇宙间的至高主权,曾写下最优美的句子:
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
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
我往那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那里逃躲避你的面。
而当神六上天、火箭飞升,地上的百姓欢腾不已,就把这样的颂赞转而献给了国家。一个“窃听风暴”的国家升级换代,成为一个居于高天之上、“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的国家。我们还能往哪里躲避他的面呢。国家的“白日飞升”,使大地上拆迁安置的百姓,更加地状如蝼蚁。于是就连手机式的呼召和超级链接,也与一个无所不在的国家偶像密不可分。
民工聊天时,响起了“好人一生平安”的铃声。那个“许文强”说,今天奉节县里哪里还有好人呢。他们开始憧憬收入高、死人也多的山西煤矿。电影末尾,一群民工跟着煤矿工人去了山西黑窑,在废墟上,他们看见一个人在两座高楼之间,拿着一根竹竿走钢丝。这是电影中最后一个超现实的意象。
飞天与落地,无数灵魂活在离地面三尺高的地方。高于大地的公义与救赎,在这部电影中依然是缺席的。超现实怎么去超,人在历史中如何转身,听见生命中一个真正的、甚至唯有一次的呼召。人们面向三峡,击节叹息,想起了陆游的《楚城》,“一千五百年间事, 惟有滩声似旧时”。
迄今为止,华人电影中,至少有过三部以三峡淹没为背景的电影。主题都异乎寻常地接近。法国华裔导演戴思礼的《巴尔扎克与小裁缝》,人过中年的刘烨来到三峡库区,寻找知青时代被淹没的爱情,当年的小裁缝却已背井离乡。香港女导演许鞍华的《男人四十》,同样人过中年的张学友和梅艳芳,一边看三峡纪录片,忘情背诵李白的诗句,一边把烧糊的饭和烧糊的婚姻丢在一边。
另一部是章明的《巫山云雨》。若没有《三峡好人》,这就是大陆电影在三峡事件上的独唱了。在即将被拆迁的巫山城,长江信号员麦强泅水渡过巫江,去寻找他巫山梦里的情人,旅行社服务员陈青。这一场戏的惊心动魄,与移民建筑的拔地飞升,在“寻找”的议题上如双子星座一样相互辉映。一个是水平方向上的绝唱,一个是垂直方向上的叫喊。
但哀伤是方便的,盼望却艰难。泅水,在本质上已不是一种期望,而是一种挣扎。就像贾彰柯在电影中将“烟、酒、茶、糖”这些不会被淹没、也不应被淹没的生活细节,特别用静物的镜头单列出来,标上名称。仿佛构成时光流逝中值得珍惜的幸福元素。也使“好人”这一理想再次被非道德化。
“烟、酒、茶、糖”所蕴含的回到现场、回到常识的原生态的生活方式,能够构成一个呼召,去拯救被流放的生活吗?有可能赋予一种被拆迁的生活以尊严吗?这一系列的静物镜头,显示出贾彰柯对生活苦难及其盼望的持续关注,开始向着一种文化的保守主义软着陆了。可惜在我看来,这些静物并不是被保守,而是被囚禁在了一厢情愿的镜头中。生活已经洪水泛滥,拿得出手的理想却是一块化石。
民工们追随一个 calling,离开奉节,去了汾阳。当初亚伯兰追随耶和华的呼召,离开了繁华的吾珥城。在那里,他拥有数十间房屋的豪宅。但从此他一生中再也没有住过房子。亚伯兰每到一个地方,就做两件事。一是为耶和华他的神筑一座坛,一是支搭帐篷。在圣经中,他被称为“义人”,也就是好人。
上帝的拣选与呼召,是恩典闯入历史的开始。当亚伯兰舍弃了他的房屋,上帝就把一个不可摇动的国赐给了他的后裔。在整个人类中,至高者的 calling 偏偏临到了他,并借着他一个人,将一个应许给了地上的万族。《创世记》记载了这一应许:
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
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
今天,全世界大约有 20 亿人相信这一应许和盟约,大约 40 亿人并不相信。但是,几乎每个人都愿意相信“好人一生平安”或“老天爱笨小孩”。矿工和女护士看见的 UFO,或者有意义,或者毫无意义。我走遍每一家影院,看见人们铺天盖地去看《黄金甲》,却几乎找不到一间放映《三峡好人》的厅。如果 UFO 无法带来一个真正的呼召,这一票房景观也很容易理解。年轻人去电影院,一边看周杰伦,一边发手机短信。他们要的就是一个超级链接,而不是一个呼召。贾彰柯的电影足够力量告诉我们生活的真相,却缺乏一个真正超自然的异象,说服人们那样的生活仍然配得赞美。
该忘怀的已经忘怀,该幸福的还没有幸福。每个人的年华老去,都在等待一个结局。或者被流放,或者被呼召。或者像苏武,或者像摩西。或者火箭上去,或者我们下来。在水平的方向和垂直的方向上,你或者继续沦陷,他或者继续仰望。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