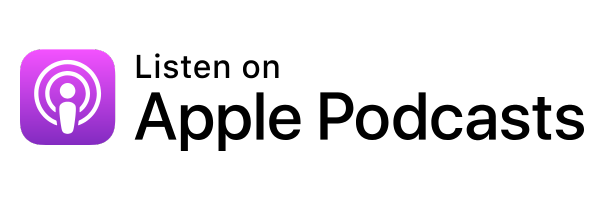把手指放在善恶交界之处,就可以碰触上帝的袍服。——纪伯伦
久违的蒙面侠佐罗,叫我想起 2001 年的墨西哥。不是一个人蒙面,是整整一支军队蒙面,原扎巴塔族的游击队人人戴着黑头罩,和一大帮国际左翼名流如好莱坞导演奥利佛·斯通,法国的密特朗夫人等,一路进军到墨西哥市的宪法广场。一场维护印第安人权益、同时反抗全球化的浩大路演,不是电影里一对佐罗父子耍花枪,耍得出来的。当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沙哈玛戈也在场,他说了句配得起身份的话,“他们蒙面,是为了更容易被看见”。可惜这句蹩脚的话,把蒙面的涵义矮化到了一个做秀的水平上。
蒙面侠佐罗,是 1919 年一部小说中的墨西哥传奇人物。在短暂的电影史上被不厌其烦的搬上银幕。上世纪 80 年代,阿兰·德龙饰演的法国版《佐罗》风靡中国,那时人们还分不清佐罗和李逵的区别。佐罗的剑术和风流迷倒了众生,他的贵族身份和“右倾投降主义”就没有被广大群众及时揭发出来。到了这部电影,佐罗摇身变成了“佑罗”。电影描写原西班牙殖民地的加利福尼亚,举行全民公决加入美国联邦,成为美国的第 41 个州。电影中有一伙来历不明的歹徒破坏选举现场,佐罗老当益壮,再次蒙面登场,用他的剑捍卫自由民主。这样,一个“杀富济贫”的佐罗,在 2005 年演变为一个立宪主义者和联邦主义者。但我想不通的是,当佐罗被带入一个宪政民主的宏伟叙事后,他为什么还要蒙面呢?
这些年来,各种“蒙面侠”电影在好莱坞有铺天盖地的声势。《蝙蝠侠》、《蜘蛛侠》、《超胆侠》等,直到你根本分不清他们的名字和业绩。不过佐罗也不是这个模式的起头。比佐罗更早的,是 1905 年英国女作家 Baroness Orczy 的小说《红花侠》。描写法国大革命期间, 一个英国贵族为了拯救断头台上的法国王室血脉,他不断潜往法国,化身为蒙面侠。每次解救成功就留下一朵红花为记。一位法国女优奉命调查,找来找去,这位侠士竟然就是她那位整天混迹于巨室,平常看起来像草包、闻起來像饭桶的丈夫。这个故事也拍过电影,但我找不到。常看电影的会想到佐罗,几乎一模一样的段落。佐罗不蒙面的时候,连他儿子都瞧不起他。蒙面时勇敢,不蒙面时怯弱,这是蒙面侠电影的一个基本框架。暗示着蒙面代表了一种英雄品格,不蒙面的时候却是生活和世俗的奴隶。读过武侠的,就会想起古龙笔下留花为记的《楚留香》了。
蒙面人都是反抗者——不然蒙面干什么,换言之就是一个蒙面的自我伸冤者,像《V 字仇杀队》中那个带面具的 V。又想起那部《面具》了,其实放在神学中,蒙面也是一个位格议题。人为什么要离开自己的思想、情感与意志,隐身在另一个身份里去行侠仗义,动用私刑。就像今天网络上的人们隐身在一个 ID中畅所欲言或破口大骂,其实是一种位格的漂移、偷渡和重叠。回到施行审判的主题,一个人对社会义愤填膺,但他的位格却不能支撑一个超乎众人之上的审判者角色。尤其在世上也有审判机制的情形下。人们对法制失望,痛恨贪官循吏,难免会呼唤一个超越在法官之上赏善罚恶的“执法者”。就像呼唤一个微服私访的钦差大臣。如果皇帝不能派这么一个钦差出来,人们就希望老天爷直接派一个下来。
换言之,“蒙面侠”是在政治国家之外,私人对于上帝主权与位格的另一种僭越。尤其当一个蒙面侠留花为记的时候,这种僭越就更明显了。因为他精心经营着一个品牌,即一个超越在国家之上的审判者的位格。蒙面侠与国家主义在本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在人间裁断生死的偶像。一个人站出来接收国家的主权,却不能凭他个人的位格,于是以蒙面来冒充上帝的代理人。如在主后 8 世纪 70年代,有一个被称为“蒙面先知”的波斯人,曾领导了一场反抗阿拉伯帝国的“蒙面人起义”。据说这人其实是默夫城的一个洗衣工,但他一蒙面就自称真主安拉的化身,并要求所有加入者都必须蒙面。所以大家也不知道他的底细。我的阅读所见,这大概是人类史上唯一一次“蒙面革命”。墨西哥的那一支蒙面军,既有对佐罗的效法,大概也有从这里下来的影子罢。
但也有一种消极的蒙面,只满足于自身位格的隐藏,并不去刻意营造一个 ID。于是行为者的位格消失在公共空间,这意味着行为者对位格内涵的一种放弃。一个位格者的尊严来自他的内涵,也来自他担当决定的责任能力。如果一个蒙面侠“替天行道”之后,仅仅像一个普通罪犯那样逃之夭夭。这就等于把自己贬低为了一个非位格的存在。换句话说,他在一桩公共事务中,只呈现出了作为生物的那一部分。他把自己的身体当作一把剑或一块石头用了一次而已,却没有呈现出他被称之为人的那一部分。所以在他的行动中,他不但不是一个具有位格内涵的执法者,而且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就像人们庆幸一个贪官被狗咬死了,却不会去赞美那只狗。就算被这只狗咬死的,碰巧都是奸恶之人,你也不会称这只狗为英雄,因为它没有能够担当这一荣誉的位格内涵。
我的结论是,蒙面的惩戒不是惩戒,一切公共生活中的蒙面行为,都不能承载任何道德价值。就像那个“蒙面人起义”,听起来就自相矛盾。“义”是位格者之间的一种关系,既蒙了面,哪里还有“义”可以举得起来呢。
极有意思的是,在希腊神话和《圣经》中,都有一个与蒙面有关的审判故事。一个是著名的蒙眼女神忒弥斯(Themis),在古希腊神话中代表法律和正义。据说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失和,没有谁可以充当裁决者。忒弥斯挺身而出,用一块布蒙住自己的眼睛,于是诸神都接受了她的裁判。这不是讽刺,恰好相反,忒弥斯的蒙眼代表了法律的一种自我节制。它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边界在哪里。在古埃及,底比斯城的司法曾被认为是最公正的,因为那里宣示神谕和主持裁判的祭司都必须断手闭目。断手就拿不到不该拿的东西,闭目也看不见不该看的事。冯象先生曾提到,在文艺复兴时期,市民们不满司法的腐败,便以“断手闭目”的法官画像,来提醒政府敬畏上帝的律法。
蒙眼女神是一个令人心惊肉跳的、对人间司法的象征。在伦敦的老贝利法院和香港的最高法院,迄今仍能看到蒙眼女神的塑像。白袍、金冠,蒙眼、闭嘴。左手提天秤,右手举剑。女神的蒙眼,暗示着她并不是真正的法律之神,她的审判也不是真正的审判,而是对审判的一种模仿。那真正的公义和审判都远在她之上,使她不得不对自己身处的位置恐惧战兢,因为那是一个本不该由她去占据的位置。
在《出埃及记》,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上帝的律法。下山后,他的脸上因见了神的面而发光。众人恐惧,怕因这光而死亡。摩西于是用帕子蒙住脸,向他们宣讲上帝的律法。讲完之后才将帕子去掉。
一面是人的激情、罪孽和偏见,一面是上帝律法的全然圣洁、公义和良善。这两个故事恰好各说一面,如果说忒弥斯的蒙眼更多是出于对前者的自觉,摩西的蒙面却更多出于对后者的敬畏。蒙眼女神提醒每一个法官,你不过是众人中挑出来的一个。你的法庭是罪人审判罪人,不是公义本身的审判。假如这个世界没有神,那就断手闭目吧,否则审判就不能成立,因为没有一个和众人一样的人配称为“法官”。除非有这样一人: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希伯来书 4:15)
而摩西的故事透露出一个旧约的观念。就是人是有罪的,人不能见神的面。先知以赛亚曾在异象中看见上帝在高高的宝座上。他惶恐不已,说我有祸了,我要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神的律法就是他的话语,就是道。以色列人后来将刻着律法的石版放入约柜,供奉在“至圣所”的幔内。这幔内之地也唯有大祭司一年一度才能进去。当摩西一人上山领受律法,他的脸因上帝的荣光而“面皮发光”。这光尽管来自上帝,却在摩西脸上并不持久。即使这样众人也恐惧战兢,叫摩西诵读律法时不能不蒙上帕子。
不但人间的法律不是全然公义的,摩西的帕子还表明,即使上帝颁下全然公义的律法,却没有全然公义的人可以诵读和倾听。在公义与我们之间有一个罪的阻碍,需要一个帕子来遮挡。这一启示就比蒙眼女神的故事更加尖锐、更令人心惊肉跳。一个法官不但需要在他同类面前蒙眼,更需要在律法面前蒙面。不但需要在人前的谦卑,更需要在上帝律法面前的俯伏敬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虽有全然公义的律法,但人的罪却没有因着恩典被完全赦免。因此没有人能够完全倾听这律法,完全行出这律法,以及完全依据这律法去施行审判。
使徒保罗谈到这个故事时,说“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到那将废者的结局”。将废者的意思就是赦罪的恩典,将有一天会成全这律法。保罗说,以色列人“直到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这帕子还没有揭去”。他们每逢诵读摩西律法的时候,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他进一步说,只有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信他的人而死,成为罪人与上帝之间的“中保”,就替代了这蒙面的帕子。
在香港电影的法庭戏里,常会见到一个英国司法传统的场景。法官在宣判一个人死刑之前,会拿出一面黑色的帕子蒙在自己头上,然后宣判。这与蒙眼女神的喻意相去甚远,更接近摩西故事的意义。死刑是人间审判权的极致,也应是人间的公义所能达到的一个极致。康德曾说,“死刑的唯一正当性就是它的公正”。
但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判决(死刑),需要一个绝对意义上的公正。人间的审判怎么可能保障这一点呢。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说,欧洲的作家通常都反对死刑,但欧洲的哲学家们通常都不反对死刑。“因为对他们来说,死刑的正当性就等于国家的正当性”,一个不能杀人的国家还能叫国家吗?因此他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死刑仍然具有一种世俗的“宗教性”,是对“国家宗教”的一种献祭。换言之,“死刑”其实构成了国家崇拜的一部分。但当一个英国法官蒙上帕子宣布死刑时,它的意义恰好相反。被蒙住的是一切人间的法律,国家的主权,以及法官本人的位格。这个仪式不但表示一种怜悯,更加暗示着,即将宣示的这一判决不是任何人有资格作出的,也不是任何国家立法可以擅作主张的。它表明这个法庭的审判虽然遵循了“程序正义”。但它仍然认为一个死刑判决不是“程序正义”可以完全支撑的。宣布一个人将被他的同类处死,这件事的严重性,使一个国家和一个法官必须去依据和仰望一种更高的律法,这只能是宇宙间的公义者透过这个法庭所作出的一项宣判。法官和蒙面侠一样,都以蒙面来隐藏自己的位格。但他是出自敬畏,而不是出自僭越。
假设我们的立法者,在法案通过的时候都蒙上帕子,说我有祸了,这将要通过的法律是如此公正,是我的污秽和偏见不能去看的;因为“立法者”实在是一个我承受不起的身份。如此我们生活中的恶法一定会大大减少。或者我们的法学家四处巡回讲解《物权法》的时候,也蒙上帕子,说我要讲的这部法律其中有公义、圣洁和智慧,都是我不配的;因为“法学家”实在是一个我担当不起的角色。如此我们的法学家也多少会赢得民众的一点尊敬了。
今天,很多国家的法院大厅或大法官的椅子背后,都刻有摩西领受的“十诫”。但没有一个国家会在议院和议员的道具上刻上“十诫”。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为什么“十诫”总是被刻在法院、而从来不被刻在议会呢?一个俏皮的答案是,如果刻在议会里,议员们就要失业了。另一个答案是,因为一个法官信奉更高的律法,而一个议会却信奉他自己。
回到这部流行电影,无论佐罗是左派还是右派;“蒙面侠”都不是英雄,而是狗熊。中国人说,大丈夫坐不改姓,行不改名。意思是位格的隐藏就是责任伦理的丧失。所以我可以使用一个固定的笔名,但不能使用一个非位格化的 ID。除非我不打算在这个“面具”下批评任何人与事,也不打算与他人有生命的交通。
一个蒙面人在人间动用私刑,不但冒充了一个蹩脚的法官,也冒充了一个傲慢的立法者。这是对人间的审判及其公义的颠覆,和对上帝至高主权的偷窃。这样的人只能被称为歹徒。他敢蒙面,恰恰因为他不承认正义女神的蒙眼布,也不承认摩西的帕子。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