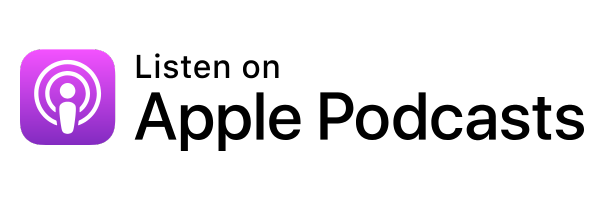在二十世纪的革命中,颇有意味的一件事,是圣经中“巴别塔”的比喻曾被一再地提及。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掀起一个修筑纪念牌、纪念塔的浪潮。1919 年,列宁委托雕塑家塔特林,叫他设计一座高达 400 余米的十月革命纪念碑。塔特林在这一年底完成了图稿,命名为“第三国际纪念碑”。他的设计是一个巨大的钢铁和玻璃柱体的上升螺旋体。塔尖直指天端,当时的舆论惊呼说,这碑塔“仿佛具有一种冲破地心引力的宏伟气势”。
这个像巴别塔一样难以企及的设计,震撼了苏联几乎所有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他们在一个艺术家宣言里,称塔特林的设计稿是共产主义的完美象征,甚至是一座“三位一体的、新的未来殿堂”。幸好,这个纪念碑实在难度太高,列宁虽然舍不得,还是就此搁置了。几十年过去,苏联成为历史,这个新的“巴别塔”也永远以手稿的形式,矗立在人类艺术史上,叫人唉声叹气。上世纪 5 0 年代,周恩来在一个讲话中,也称共产主义革命是“建造通天塔的宏伟事业”。甚至经过文革的灾变后,这个气势不凡的比喻还是没有被放弃。胡耀邦在“拔乱反正”中对科学界的几次讲话,都提到巴别塔的故事。他还特别给数学家华罗庚写了封信,鼓励知识分子捐弃前嫌,共同建造社会主义的“通天塔”。
大多中国导演的叙事,基本停留在古典评书“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手法上。像《巴别塔》这种多线交叉的叙事模式,真是很少见。墨西哥导演冈萨雷斯说,他的电影企图表达全球化时代人类彼此交流的种种困境。电影涉及四个国家,三个故事,四种口头语言,及无数的肢体表达。都因一次被误以为恐怖主义袭击的少年人的枪击意外,而像蝴蝶效应一样地关联起来。
圣经说,上帝吩咐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那么人的后裔形成不同的族群与城邦,作为治理这地的形式,对此圣经并没有直接指责。但是人类的第一座城却是该隐在杀弟之后建造的。耶和华放逐该隐,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却不服气,反而建了一座城,并以他儿子的名为这座城命名。在大洪水的审判中,该隐的后裔连同城市文明一起毁灭了。洪水过后,挪亚三个儿子的后裔散布各地,各随支派,“在地上分为邦国”。这是城市文明在大地上的第二次出现。修房和筑城,对人有一种极大的试探。房屋和城邦的出现,意味着人类开始拥有“不动产”。我有一些朋友好容易买了房子,常常就这样说,“终于有自己的小天地了,总算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了”。门一关,就是自己的世界。自己就是自己的王了。
这就是英国谚语“国王的权力到我的篱笆为止”,或“我的财产就是我的城堡”的意思。所谓小天地,是对宇宙的模仿。肖厚国先生说,于是一间房屋的修建,便具有了与创世同等的意义。在有限的时空中,我们再选定一点,用各种材料搭建一个“占山为王”的地盘。房屋和城邦的建造,就仿佛宇宙的开启和秩序的形成。阿伦特曾说古希腊人对房屋的态度,并不是今天理解的对个人权利的尊重。而是出自一个宇宙间的事实,“倘若一个人没有一所房屋,他就不可能参与世界事务。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
这样,国家主义就成为随国家而来的一种试探。人们不但需要一座城邦,还需要在宇宙当间,给它树一个顶天立地的位置。人们把安全感放在了房屋的四壁,和国家的四面城墙之内。建造一座城邦,就成了对上帝至高主权的一种集体叛乱。尽管当国家主义形成后,房屋成为私生活的一个堡垒,和千百年来个人在大地上对国家主义的一种抵抗。一座城邦是国家主义的,一间房屋是自由主义的。但是当我们疲惫时渴望回家,心想那是我的精神港湾,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其实我们和国家主义者也差不多,把自己的不动产变作偶像,把我们与上帝、与他人就与世隔绝了。
一个大地上不可摇动的国,永远是人心中难以克服的试探。于是挪亚的后裔开始了巴别塔的故事。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神就变乱他们的语言,真就把他们分散在全地了。
自从示拿平原上这一巴别塔事件以后,每个人心中难免都有一座巴别塔。今天,汽车飞机可以把陌生人的身体运送到地极,而语言、种族、家族、国家、宗教,以及肉体本身,依然把人的灵魂封闭在一面自我中心的墙内。什么东西构建了你的小宇宙,割断了你与上帝及人类的交通,什么东西就是你的巴别塔。我在成都的一座汽车站内,看见一块提示牌写着,“不要和陌生人搭话”。原来电影中美国游客因枪击事件滞留在摩洛哥小村里的那种恐惧,并不十分遥远,其实离我的家只有十分钟路程。那标语离我那么近,电影却离我那么远,你不能不在心里悲叹,知道人类真的被诅咒了。这诅咒给了近处的人,也给了远处的人。给了祖先,也给了后裔。但我一直以来,常会轻轻地放过自己,而去怨恨那些修筑第一座巴别塔的家伙。
《创世记》中记载,挪亚的后代彼此商量,“来吧,我们要作砖,把砖烧透了”。把砖烧透,需要至少摄氏一千度以上的高温,这是示拿平原上的“乌拜德文化”的一项主要成就。它们建的这座城就是巴比伦。在《启示录》中,这座城被视为整个堕落世界的象征。巴别塔的第一层意义,就是对这座城的加冕和命名。这是人类的第一次宗教行为,人类第一次对偶像的集体膜拜,以及对“国家”这一偶像的第一次献祭。为了“传扬国家主义的名”,人们背弃了他们的祖先挪亚所敬拜的上帝,也就是从大洪水中拯救了人类苗裔的上帝,转去膜拜自己的建筑物。巴比塔也是第一座神庙,是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在历史中粉墨登场的一个起点。从此人就不要信仰中的启示,而要宗教中的构建。不要我之外的拯救者,而要自我实现,自我修行,自我体认和自我逍遥。直到今天,就如这部电影用一种开放性的多头结构,所拼贴出的一个当代的人类场景:身体的全球化,与灵魂世界的破碎不堪。
在第二层的意义上,巴别塔也是人类在上帝面前的第一次“有组织犯罪”。魏勒夫曾将治水模式视为东方专制主义兴起的渊薮。他说,大规模的治水工程,刺激了政治国家以专制主义的方式组织起来。其实“东方专制主义”也有两种,一种是远东的治水模式,这是在水平面上展开的一种人类乌托邦。从大禹王朝到三峡工程,中国人永远都喜欢把桃花源安置在曲径通幽的大地上。另一种就是中东的巴别塔模式,这是一种在垂直面上展开的人类乌托邦,它的核心是以人为神,以高耸入云的纪念牌,去替代高耸入云的圣山。
治水模式导致的是一种非宗教性的专制主义。而巴别塔模式发展出的,是一种政教合一的专制主义,即一种最彻底的国家主义。这种国家学说从古代巴比伦开始,直到波斯、罗马,再透过启蒙运动中的卢梭和黑格尔等人,一直通往各种现代的极权主义。在这样一个“全球化”视野中回望 20 世纪,原来中国的百年历史,就是这两种东方专制主义模式在西方晃荡两千年之后,在远东的一次会师。
“传扬我们的名”的结果,从来只是传扬了某些人的名。“历史之父”希罗多德说,他曾在公元前 406 年游历巴比伦,看到一座高达 201 米的“通天塔”。这是人的一个毛病,宁愿相信一个历史学家,却不太相信被称为上帝之言的圣经。1899 年之后,在新巴比伦城的遗址考古中,又陆续发现了许多“通天塔”型的建筑。一些砖片上刻着“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的国王,众神的护卫者,那波帕拉沙尔的儿子,巴比伦之君”。整个人类受的苦,就传扬了这么一个名字。
当波斯征服巴比伦时,居留士大帝也为“通天塔”所倾倒。后来希腊征服巴比伦,亚历山大大帝又为通天塔的宏伟废墟再次折腰。人与城邦的光荣与梦想,甚至一度也诱惑了上帝的选民,使巴别塔事件在以色列史上也重演了一回。以色列人羡慕人家都有国王,就不愿承认耶和华神是他们的王,也不再喜欢先知、祭司和长老这样分立的治理模式了。他们就缠着先知撒母耳说,我们也要像列邦一样有自己的国王,有自己的巴别塔。
《撒母耳记上》如此记载,“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作他们的王”。
从此,地上的万族中,人都作了自己的王。
两年前,我参加一个国际作家会议的圆桌讨论,题目是“巴别塔与人类的表达困境”。一位从伊朗流亡到美国的学者,说当年在伊朗负责电影审查的官员是一个盲人。他需要一边拿剪刀,一边有人给他讲解电影内容。这位学者说,作家面对当代世界的唯一出路就是“大声的写作”。这是利用“通感”修辞的一个巧妙说法,中文的传统用语叫“掷地有声”。电影本质上就是这样一种艺术,叫瞎眼的能听见,耳聋的能看见。所谓“通感”是人与人的交流超越了感官,走向位格互动的一种跳跃。譬如一个朋友曾借俄罗斯电影《毒太阳》去看,完了还给我,说片子太棒了,可惜没把中文字幕调出来。我说这样你也能把它看完?她说没问题啊,非常感人。
电影中,有一个日本聋哑少女的故事,叫我想起这个“大声写作”的观点。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段落。哑少女的焦虑被困在了身体之内,尽管哑语和彩屏手机,可以延伸她与同伴的远距离交流。但当她站在另外那些灵魂的面前,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只剩下了肉体本身。她尝试用身体去向人分享她的生命,却在焦虑与失败中陷入了一种比沉默更沉默的幽暗。这段故事把“语言”和“沟通”的主题延展了。有人从政治隐喻的角度,说富裕起来的日本就像这个女孩,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没有话语权,她不能被听见,只能以肉体欲望的方式被看见。我不知道这是否导演想放进来的一个意思。
但这涉及我要说到的第三层意义,巴别塔事件也是人类的第一次全球化。人类聚集、迁移、围城、筑塔、称帝,然后被“分散到全地”。主后一千年间,福音的传扬则是第二波的全球化,要将灵魂被隔离的人,重新在基督里成为一。而近代启蒙以来的理性、技术与市场,则是人类的第三次全球化。今天借助于交通、通讯、媒体和商业,借助抽象的数字和具体的肉体,借助网络及其屏蔽,也借助电影及其盗版,全世界有耳可听、有眼可看的人也在继续聚集着。
这三次全球化的并存,就像这部电影一样多线索共存,勾连起五千年的人类史。美国学者卡斯说,今天的人类“利用象征性的数学”,再次拥有了“同一种语言”。一个技术性的、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的社会“将使我们再次面临巴别塔的命运”。英国政治学者奥克肖特也说,“许多世纪以来,我们文明的主要力量是被用来建造巴比塔”。他说,一个孤单的人为得着安慰,常常会夸大自己少数几位朋友的才华,“我们也是这样,常常夸大那些人为的理想,来填充我们道德生活的空虚”。
换言之,这第三波的全球化,就是巴别塔的卷土重来。看这部电影,你会说,世界已到这个地步了。导演在他的故事之上,使用圣经中“巴别塔”的典故,究竟是对新的“巴别塔”之路的批判呢,还是对它流露一种人文主义的盼望?他给出了鲜活而破碎的场景,但对他的梦想到底放在那里,却不露声色。
对我来说,“巴别塔”也可以是一个温暖的隐喻。因为它提醒我们一个常被这世界否认的事实,即人类的同根同源。《创世记》记载,“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这就是巴别塔事件的背景。就像我的一个朋友对儿子的教育失去了信心。一位牧师说,重要的不是你儿子现在是否听话,重要的是有一天当浪子回头,他知道要回到哪里。他知道有一个起点,爱他的人在那里立下榜样,并一直为他的灵魂守望。
就算我有机会住别墅,我知道我也是寄居的。就算我有一张公民的身份证,我知道我也是客旅。那最初造人的,也能叫人成为一。那帮助我们离开罪孽过犯的,也能帮我们最终离弃一切的偶像。
就如舍斯托夫在他的《旷野呼告》中说,“离开黑格尔走向约伯吧”。离开巴别塔,仰望圣山。离开我的文字,开始祈祷吧。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