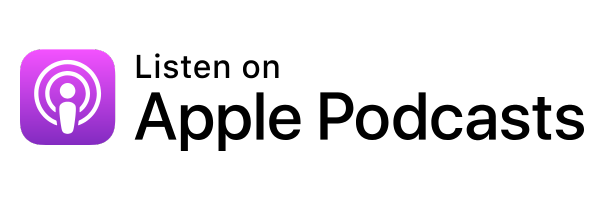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注:2006 年 5 月,三位基督徒知识分子在白宫与布什总统见面,其中因杨茂东(郭飞雄)先生对我和余杰弟兄的指控,而被称为“白宫事件”。当时我在小范围内发表了这份道歉信。后来杨茂东兄被官方逮捕,我停止了一切关于此事的发言,不再为此事辩解。然而这一事件不但标志着我个人、也标识着当代中国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在信仰中对国家社会的关怀,与非基督徒知识分子的自由民主理想的差异和冲突。因此,在杨茂东出狱之后,我将此文收录在此书中。几年来,我为此恒切祷告,祈求主基督的十字架,能在这块土地上,替代和释放一切被缚的普罗米修斯。)
尊敬的杨茂东先生:
您好。5 月 8 日中午,我与傅牧师一道,在对华援助协会的办公室告诉你,我和余杰的决定。我们二人不愿与你一起前往白宫参加与布什总统的会面。作出这个决定对我来说是困难的,但也是坚决的。我完全理解这件事对于你个人的伤害。也愿意在此公开的向你诚恳地表示歉意。我也愿意为此决定负担可想而知的舆论和道义上的一切指责。
我们交往已数年。2002 年你请我去四川遂宁作布云乡长直选的田野调查,后因为我们对直选的看法迥异,我拒绝了对该次选举进行宣传推广的出版计划。这件事得到了你的谅解。在这件事上你对我的学术与政治立场的尊敬,使我一直对你保持敬意,也由此将你视为同道的朋友。在你的小说《李世民》中,你的一些想法和政治理想,开始使我产生距离。2005 年你组织了反日游行,撰文抨击焦国标等。你的民主理想中所蕴含的某种民族主义与孙文主义的情结,开始使我忧虑。你在因此被羁押时期的绝食行动令人尊敬,但这一事件本身我仍是坚决反对的。
我和余杰也的确私下劝说,与你合作的主内弟兄,与你的道路保持距离。但在太石村事件中,你的勇敢和担当,却重新赢得了我极高的敬意。你在出狱后所说的“不流血、非暴力和无敌人”,这三个合符《圣经》教导的原则,几乎令我彻底改变了对你的看法。
我来美国是参加“中国的宗教自由与法治”研讨会,这是傅牧师的邀请函上所载明的主题。傅牧师领导的对华援助协会,长期以来关注中国家庭教会的维权和中国的宗教自由。尽管因为所谓“政治化”而被一些教会疏离和排斥,但海内外大多数基督徒和广泛的维权人士,都很尊敬和感谢他的工作。如我曾参与辩护和调查的蔡卓华案和华南教会案,都和对华援助协会的长期关注和支持有莫大关系。
但我和余杰来到华盛顿后,才知道你也与会。尽管略有诧异,因为你并未信徒,也未关注和参与宗教自由的维权。但我们理解,负责安排的主内弟兄希望帮助你出来走走。我在第一天也向你表示了我的个人意见,希望你能在美国多呆一段,多看多听,少表态。不过在后来几天的行程中,我们对你的一些言行产生了负面的评价。对你和我们的主内弟兄对局势的盲目判断,对某些想法的固执和膨胀,以及在与美国国会及其他部门交流中的措词和态度,产生了极度反感。在此过程中,作为你的朋友,我没有主动与你进行推心置腹的交流,尽到我对你的负担。这是这段时间来我对你感到亏欠的地方。也对我们最后的决裂负有极大的责任。
5 月 7 日下午在德州米德兰的教会,我们约傅牧师谈话,交流了对你的看法。提出既然会议已经结束,希望他不再以对华援助协会的名义,为你安排任何的见面或其他寻求资源的机会。我们认为,因你在维权运动的作为而受到的广泛尊敬,你将会得到各种机会进行交流。但我们认为,教会不宜再继续介入其中。这样的建议,出于我们作为基督徒对教会的一种责任感。就是教会的维权,要谨守《圣经》的教导,既不怕被“政治化”,又要反对“政治化”,不应介入任何非和平的的政治反抗运动。傅牧师也同意我们的看法,告诉我们你已决定将于 8 日下午离开米德兰去纽约。我们认为此事已经结束。我们的追求不尽相同,但我们彼此的关系得以保全。
但 5 月 8 日在米德兰,傅牧师忽然宣布,布什总统将会见我们四人的消息,我们才知道傅牧师和米德兰的牧师联盟一直在努力,促成美国总统公开会见中国家庭教会的基督徒,表达对宗教自由的支持。这是我们事先完全不知情的。当你在午餐酒会上讲话,宣布说,这将是美国总统近十年来第一次决定接见“中国民运人士”。我和余杰交流意见后,作出了这个决定。如果你去,这个会面的性质就是异议人士与美国总统的见面。我们二人将选择退出。我们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捆绑的见面,我们必须对这一会面之于国内家庭教会及傅牧师所在机构的影响负责。我们也感到,必须下决心结束这一次会议安排的错误了。这件事的严重性远远超过了我们个人的荣誉和得失,这也是我们和三位牧师需要在一起祷告的原因,我们必须求问上帝,仰望和寻求彼此信仰立场的合一。后来我下楼找到李柏光,告诉他我们的意见。请他自己决定或与你一道去白宫,或认同我们的意见。柏光表示他向主祷告,并一切听从傅牧师的安排。如你所知,傅牧师的决定是向白宫说明你的情况,请你退出并请求你的谅解。他的这一决定的确是在我和余杰坚持退出的情形下作出的,理应由我们来负担这一决定对你的伤害。
这些情况,我本来打算在当日一一向你说明并请你谅解。但当你得知这一情形后,当场翻脸,拒绝与我交谈,并请我出去。我感到没有办法与你交流。因此只是借与国内弟兄通电话的机会,间接向你表达了我的上述想法。并表示希望通过其他的渠道,而不是透过教会的渠道去为你寻求类似的机会。然而,随后你在震怒中所透露的一些信息令我更加震惊,也感谢上帝,让我们作出了拒绝与你一道去白宫会见布什总统的决定。作为基督徒,家庭教会的维权,既有寻求公义的一面,也有顺服掌权者的一面。同时,教会的维权,乃是为着福音的缘故,而非为了自身的权益。因此,我们绝不能把这样的寻求,与你所指称的“中国民运”并列起来。而且作为维权人士,我们的良心也不能为我们所不能认同的维权运动的某种危险的趋势背书。
从你所透露的部分细节,我才发现直到获知白宫见面的消息之前,我和余杰、柏光才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人。在我看来这真是上帝的奇妙旨意,最后进入白宫的三位基督徒,是事先什么都不知道的三位;凡知道和筹划的人,倒一个都没去成。你可能认为这是阴谋,或是偶然。但在我看来,这却出自上帝的手腕。谁能够谋国呢,谁能够谋命呢,谁又能够救世呢。谋略,谋略,中国的自由民主难道靠的只是人的谋略吗?信仰的自由,难道靠的只是谋略吗?在我们,依靠的是对上帝的爱与公义的仰望。在非基督徒的秋风兄看来,依靠的是道德力量的积累。那么杨兄,在你那里,到底靠的是什么呢?很抱歉我在此请求你的原谅,也期望你能在这件事上看见人的作为的有限与落空。你的机会和依靠,事实上的确被我们断送了。但我们却希望将我们所依靠的,送给你。我也希望我在国内的弟兄,也能在这件事上看见自己凡事陷在谋略之中的危险,回到对上帝主权的单纯的信靠上。
我们也都知道,在你的努力下,美国的国安会,在这次会面前,特别对此事作了调查和评估,阅读了你以前的文章,重新评估了你的努力,也最终作出了他们自己的决定。没有人能替白宫决定他们的总统要见什么人,所以,我也必须说,决定你不能会见美国总统的,是美国政府,而不是我和余杰。但是,我和余杰有权决定自己是否退出。我们的个人良心的决定,不受任何人的所谓投票和所谓民主程序的制约。我们的退出,被理解为伤害了你的利益,并在事实上导致了你失去这一机会。我坚持认为,这一次会议安排一开始就存在某种不讨上帝喜悦的错误,最后,以我们扭转这一错误并因此对你造成伤害的方式结束。我为此向你表示我的歉意。并且我也必须承认,我对你的某些评价和观察也有可能是片面和苛刻的。如果今后证明我错了,我当再次向你致歉。但当我和余杰一致认为与你一道见布什的后果可能更严重时,我们很高兴选择了目前的结果。
我想,假如各种分歧和安排能够在事先被讨论,就不会导致最后这尖锐的分裂。所以我的一贯看法,在寻求正义的事上,谋略就是地狱,无论对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来说,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是非的界限都是简单明了的。出自道德,不出自权谋;出自敬畏,不出自血勇。希望你能接受这句话的劝告。我们三人作为参与信仰维权的基督徒知识分子,与布什总统的这次见面,本可有着双重的理解、意义和推动。但你的公开信,将教会的信仰自由,与维权运动的民运化的分歧,以公开决裂的形式表达了出来。也将保守主义的维权运动,与激进主义的维权运动的分歧显明了出来。这几天来,我一直在想,我也感谢你这封信,这也是上帝在此事上一直掌权的证明。分歧的公开不一定是坏事,我们今天决裂了,一个简单的原因,是因为我相信基督的十字架,而你不相信。中国的未来需要的不是无原则的统一战线,而是彼此客气的“市场细分”。之前我在此事上的态度是默然不语,不愿对你和其他人有所批评。但几天来我考虑再三,决定写这封信,既在此事的后果上向你道歉,也同时叙述事实和我个人对你的看法,向天下的知识分子公开表明我的信仰立场和对你的反对立场。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在心里仍将你视为朋友,如我这次对你说的,我对狭义上的政治事务不感兴趣。但我和无数人一样,也期望看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家的出现。当某种现实的、自由的政治制度来到时,我甚至乐意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将我的名誉和努力为那些值得尊敬的民主政治家背书。但在今天,我们要走的路是如此不同。我真诚的希望,这一次分裂能以我的道歉结束,然后各自努力,彼此尊重,彼此祝福。因为不相为谋,不等于相互怨恨。在纽约,曾有朋友出面邀请你与我一起聚餐,化解冲突。那天,我去了,期望能有一个向你当面道歉的机会,但我能理解你不愿来的心情。5 月 8 日后,我们曾多次在一起为你祷告,求上帝平息你的愤怒,并借着这件事,使你认识到主耶稣比美国总统更大,十字架比自由民主更好。如果这一事件使你远离了上帝,求上帝将这罪归在我和我的子孙身上。我作出了这个不后悔的决定,也背上了这个十字架。在你未成为我的主内弟兄之前,我的祷告将无法止息。
与你持不同政见的基督徒朋友:王怡
2006-5-22
附:《我对大陆维权运动的立场》
2003 年以来维权运动的兴起,使大陆在 1989 年之后再次出现了各种政治异议活动在主流社会的公开化。我所理解的维权运动有三个立场,一是法治立场,围绕受侵害的公民个体和诉讼程序,动用一切法治技术和言论空间进行权利的抗争。二是公民立场,尤其借助互联网所提供的低成本的信息沟通与公民结盟的平台,积极构筑非官方的公共政治空间。三是政治立场,任何一桩案件都是当事人的维权,但只有那些对政体变迁具有启蒙、动员和施压效果的案例和事件,才构成一种民主化的维权运动。因此这些案件的意义的确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司法性的。维权运动日益受到海内外关注中国人权与政治状态的人们的重视。我对这一运动的现状迄今有如下的观察和立场:
1、在今天的中国,异议活动趋向公开化,镇压手段趋向黑箱化。表明追求自由与公义的社会理想正在民间赢得更多的尊重和道义支持,也使专制势力在意识形态和统治技术上被迫以粗暴的方式后撤。这一趋势的发展必将促使中共在未来数年中,进行最艰难的权衡。或者以理性的方式,逐步宽容那些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民间温和力量,开始考虑政体改革的契机和时间表。或者对维权活动和异议人士的打压走向全面的非理性和政治癫狂。维权运动是中国这一百多年来对政府怀有最大善意的一次民间运动,很可能帮助中国政府放弃专制主义的捆绑,通过自由民主的政体改革,使老百姓在法治之下得自由,也使党政机器在法治之下得自由。使治理者和被治理者都免于恐惧。
2、大陆 27 年来的民主化追求出现了三种动员模式。第一种是“幕僚模式”,知识分子期望走到离政治领袖最近的地方去推动民主。在 1979 年“民主墙”运动被镇压,到 1989 年六四屠杀前夜,这是一种主流模式。直到今天,仍有部分知识分子寄望于这种模式。第二种是“民运模式”。希望提出一个全面的政治民主化的纲领,形成一个政党化的领导中心,以直接的政治抗争、街头或地下运动的方式,包括组建反对党的尝试,去改变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一模式起源于民主墙时代,1989 年之后这一模式在主流社会和自由派知识分子中长期处于边缘化地带。我不相信民运模式能为中国带来一种有效保障个人自由与尊严的政体改造,构建一个爱与公义的政治共同体。我个人对这一模式保持距离、戒心和批判,并坚决反对以秘密会社的方式和暴力的鼓动,去推动中国的民主化。但另一方面,即使有人组建反对党,这也是宪法所列举的公民权利。我将以更坚决的立场,反对政府对那些非暴力的异议人士的镇压和审判。
3、近年来形成的维权运动则是第三种模式。这一模式把个人自由的积累看得比民主化的指标更重要,把个人的地位看得比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等族群利益的梦想更重要。以个人诉求优先于群体诉求的自由主义立场,最大可能的避免而不是煽动社会骚乱。以对法治秩序的尊重来缓释对政治秩序的冲击。以对宪法人权条款的尊重去表达对恶法的反抗。以法治的程序和途径,把法律背后的专制者一步步逼到阳光下去。以直接行使宪法权利的“公民不服从”或“自力救济”的行为,累积未来政体变迁的压力和技术。以爱与非暴力的原则,化解治理者与被治理者之间一百年来的仇恨和戾气。这是我唯一推崇的方式,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坚守这样的原则。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认为民主制度若不能以这样的方式得到,民主制度就不值得我们去争取。
4、目前维权运动的基础是权益受到侵害的广泛的民众群体。维权运动的基本结构,是通过捍卫工人、农民、市民等各阶层民众受到侵害的信仰自由、言论自由、财产权等各项人权,实现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新启蒙,和与社会的新结盟。当前,维权运动主要的表达者和行动者有 9 类群体。一是以丁子霖和“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政治维权群体。他们在维权运动尚未兴起之前,便以法治方式坚持有韧性的抗争,并将 64 屠杀的民族记忆以维权的方式不间断地延续到了今天。二是以“独立中文笔会”为代表的异议知识分子群体及一部分公共知识分子。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就是尚不愿被标签为异议人士的异议人士。笔会这一异议群体的汇聚,在近年来事实上打破了知识分子的结社限制,其光谱跨越了体制内外和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三是以南方报业集团和中国新闻周刊等媒体为代表的自由派媒体。自由派的记者、编辑日益成为新闻人的中坚,推动了一批自由派媒体的形成,为维权运动在公共领域赢得了令人惊异的空间。上述三个群体的存在,使维权运动在 27 年的大陆民主化的背景中,获得了一种连续性。也获得了一种温和、理性而又坚决的保守主义品质。第四是以张思之、高智晟等为代表的人权律师和“政法系”群体。这是最近的维权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最集中的反映出与前两种民主动员模式的迥异之处。第五是以陈光诚、姚立法、刘正友为代表的乡村维权领袖,他们的本土与平民色彩,在维权运动中具有一种在道义上最令人尊敬的品质。第六是以李健、黄琦等人为代表的网络维权派。第七是以环保、艾滋病等民间 NGO 为代表的社会维权派。第八是基督教家庭教会等宗教群体在宗教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方面的维权。第九是以郭飞雄、赵昕等为代表的职业化的维权活动家,这是维权运动中走得最远、最接近传统民运模式、但相互之间差异也最大的部分。
5、维权运动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动员模式,更接近于美国二十世纪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而不同于前苏东国家的政治反抗运动。这一运动因它所受的打压和空间的急促,在目前就像一场花样跳伞,具有非组织、无领袖和扁平化的特征。不同人群在降落的过程中寻找彼此的手,在平面结网。等降落至合适的距离后,便彼此分开,在纵向结网,实现多中心的社会政治结构的软着陆。上述群体在目前构成了一个复杂和笼统的维权运动的图景。在诉求、道路、策略和目标上不尽相同。有倾向于保守主义的维权派,在公共知识分子中甚至仍有在幕僚模式与维权模式之间游离的部分;同时也存在维权运动中的民运派,对维权运动作为一种新的动员模式缺乏信心,而视其为新的政治反抗的阶段性征兆。在目前这一维权运动面临角色和道路的细分,也存在两种民主动员模式浮出水面的争论。一种是民运的维权化,一种是维权的民运化。一种是将马丁·路德·金和甘地视为一个新的榜样序列,另一种则仍将孙文、列宁或李世民视为一个偶像的序列。
6、在尊重宪法人权条款及非暴力原则之下,我尊重多元化的民主启蒙与动员模式。也尊敬每一位坚持抗争和遭受迫害的民运人士。去年在瑞典我见到魏京生先生,今年在纽约也见到了徐文立先生。我也见过王丹、王军涛、封从德等 89一代的领袖。从我知道他们名字的那一天,直到如今,我对他们孤绝的努力都充满了敬意和内心的哀伤。我期望大陆在不久的将来也出现新的公民运动和街头的民主运动。我甚至也期望看到民间再次出现真正值得尊敬的政治家。但我仍然反对在今天将维权运动民运化、街头化,甚至反对一切秘密的和地下的谋划。正如秋风兄所说,维权运动同时是一场民间道德运动。我相信中国的自由民主需要一个在爱中恒久忍耐的过程。法治化的维权运动羽翼初生,不应成为反抗运动酝酿的掩体。致力于反抗运动的人士,应该以更大的勇气和信心离开维权运动,彼此尊重,各自阐述。我将捍卫我所参与、理解和珍惜的阳光下的维权运动,反对任何挟维权运动而推动政治反抗运动的谋划。
7、在作为基督徒争取信仰自由和更广泛的宪法权利的维权中,我认为世界就是福音的工场。基督徒的信仰是全人的信仰,不是 PART-TIME 的兼差。作为一个基督徒参与中国争取言论自由和其他政治权利的宪政转型,参与基督徒依法争取信仰自由的事业,乃是为着在其中彰显基督徒的价值观和基督的荣耀。因为离开了信仰,中国仍然没有未来。在政教关系上,我不认同退缩在政治社会领域之外的信仰立场,但我也反对教会与政治的结盟,反对基督徒与违背《圣经》教导的推动方式同负一轭。我不怕因为有人把家庭教会视为维权运动的一部分,而背上政治的风险或骂名,但我也必须要在教会为着福音的缘故对宗教自由的捍卫,与维权运动的现实政治诉求之间,明确的划开一道界限。埃及是埃及,迦南是迦南,中间是一道红海。不相信上帝的人,可以推翻埃及的政权,但却不可能过红海。我认为,作为普世人权的宗教自由和基督徒的文化使命,与“政治”的确密切相关,谈政治色变的基督徒,是怯懦的基督徒,和并不真正认识福音的基督徒。但教会的福音使命却与政治无关。政治的意思,是在基督再来之前,基督徒与其他信仰或无信仰人群共享的一种社会共同体的关系。因此,在今天,基督徒争取宗教自由的努力,你可以说属于维权运动中倾向于保守主义的一部分,但不能、不会、也不应该属于反抗运动的一部分。
2006-5-13 于纽约,2006-5-21 修订。
——摘自 灵魂深处闹自由:《与神亲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