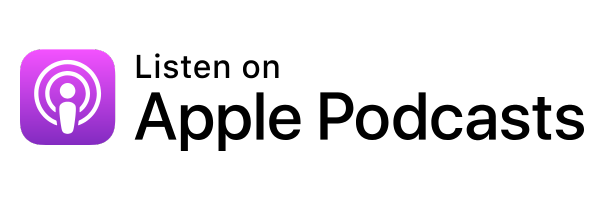清明又至。上坟、扫墓的,并不都是无神论者。道场法事,追思礼拜,人们向死而生,也是一个灵魂,各自表述。小时候,戴红领巾,扫烈士陵园。才知道少先队也有祭拜仪式。我悄悄问亲爱的伙伴,为什么团委书记也搞迷信?他是大队辅导员的身边红人。很得意地说,这是文件规定的。从此,我心头有了羞耻感,在烈士墓前,暗暗将袖子上中队长的两道杠,解下来放到兜里。
有个传道人,讲他上山下乡,怎么回了成都。毛泽东去世,乡里开追悼会。事后,问巨幅画像怎么处理?他就说,周总理都是火化,撒到海里。哥几个就怂着乡长,迈开行军步,把主席像烧了。第二天看报纸,他又去恐吓乡长,说这下完了,毛主席是不能烧的,要在水晶棺里躺一万年。几个人嚷着去告发。乡长吓得半死。没多久,他们几个就优先回城了。
这都是老成都的事。几十年来,一些人从过去剥离出来,活成另一群人。一些人还在记忆里斗争,一些人删除了记忆。就像有人是身体移民,精神还在档案里。有人是灵魂移民,身体还在现场。从这个角度说,任何一个真实的信仰者,本质上都是“外国宣教士”。因为信仰者的意思,就是在彼岸有花名册,在此岸是寄居者。
人的身份认知,也和信仰有关。在广州,我问一些买房的朋友,你们是不是广州人?他们摇头,说打心眼里,没当自己是广州人。我说是,在成都住了 18年,一直就不认为我是成都人。全国 3 亿城市居民,到底有多少人,愿把自己的命和一座城挂起钩来。到底有多少人,在一座城市信誓旦旦,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这样看,钉子户是多么珍贵的财富。没有钉子户,就没有城市文明。因为我们是随时可以撤退的。随时可以换座城市,就像换座监狱。只有钉子户是真正的爱国主义者,他们是一个社区真正的委身者,他们热爱和忠诚于政府发放的产权证。他们的品牌忠诚度,叫那些有任期的空降部队望尘莫及。
但财产或能立身,不能安命。尽管在司法上,不动产决定管辖权,是从民法到宪法,一以贯之的准则。许多导演到一座城市拍戏,也爱说,这是我来了就不想走的“第二故乡”。只是这种轻浮的言语,对钉子户们的伤害,更甚于拆迁。就像老夫老妻通奸,对每一对新婚夫妻的盟约,都是不要脸的拆台。
我是后来才明白,当初结婚,妈妈特别找了骆阿姨,给我们铺床单。因为她婚姻美满,一面贤惠、忍耐,一面还有欢喜。就像画家凡·高,一生反复引用的那句《圣经》经文,“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所以偷情的人,若不悔改,就不要出现在别人的婚礼上。掌权的人,若不委身给一座城市,就不要去拆这座城市的房子。
对我来说,是那一天,2008 年 5 月 12 日。18 年的成都户口,这之后,我才真当自己是成都人。我对我的神,重申了人生的“五个一工程”,就是一位上帝、一位妻子、一间教会、一个呼召,和一座城市。我在那个夜晚许愿,从此一生住在这座城市,服侍这座城市。
集锦片《成都,我爱你》,是陈果、崔健和韩国的许秦豪,为纪念汶川大地震一周年,杜撰的昔在、今在、永在的三个成都故事。崔健那段过于离谱,陈果拍 1976 年那段,很有四川的鬼气。许秦豪拍了一段倾城之恋。他单独拿出来发行,取名《好雨时节》。
大地震一周年的前两天,韩国人东河在杜甫草堂,遇见留学美国时暗恋过的女同学吴月(May)。这名字显然是受灾者群体的隐喻。他们若即若离的恋爱,开头像一场偷情。因为双方的婚姻状况,故意留白,不作交待。台词往来,也充满一种韩式爱情片的挑逗意味。直到机场宾馆,吴月在激情中忧伤,止住了两人的亲密。剧情这才层层扭转。原来吴月的丈夫死于地震,她在周年祭前夕,遇见曾经的恋人。行走在伤痛、怀念、迷乱与负罪感中。
大地震的场景很少。电影风格也过于小资化、广告化。但许秦豪的风格,是一贯注于孤零零的二人世界,在这部命题作文中却有突破。他说,如春雨一般,爱情来得正是时候。因为爱情在他作品中,第一次扮演了医治与安慰的功用。爱情在这里,即是个体性的,又是社会性的。既是情感的,又是灵魂的。
像“自行车”是个细致的设计。大地震当日吴月骑着车。作为一种创伤转移,她的大脑删除了自己骑车的记忆和能力。东河找到和她以前一起骑车露营的照片,这是吴月第一次被医治,她赶到机场,开始对爱情有了期待。片末,东河从韩国寄回一辆折叠单车。吴月在同事帮助下,骑上车,在杜甫草堂的阳光下微笑。这是全片最动人的画面。我想,凡在那天以后,真知道自己是成都人和四川人的,会为这个画面落泪。
最后,东河站在草堂门口,等着吴月推车,迈过古老的门槛。就像两年了,数百万志愿者站在我们身边,一起迈过门槛。如果好雨知时节,那么地震呢?如果爱情来得正是时候,那么苦难呢。丧父、丧子,丧妻,每个人都要经历。如果一生参加别人婚礼的次数,多过参加别人葬礼的次数,我们的生命就过于委琐。因为不能分享死亡,分享生命就是假的。不能分享亲人的追思,分享他人的喜事就是装的。不能分享灵魂,分享身体就是脏的。
公车上写着,“因为有你,成都更美丽”。我认为,说这话应当沉重而庄严。是的,因为有埋在废墟的孩子,有自焚的阿姨;有天伦之乐,也有孤儿寡母;有妇产医院,也有殡馆墓地;有地震,也有春雨;有警察,也有教堂——
所以电影拍得一般,但我不看不行,不写也不行。感谢朋友阿信,终于完成了他的灾区志愿者访谈录。王兰和吕康银,都是地震中截肢瘫痪的伤员。有个姐妹,一年炖了 52 只鸡给他们。春节前他们接受了洗礼。还有仁增姊妹,我为她祷告,她流泪点头,却说不出话来。
他们就是吴月。没有韩国来的情人,但有天上来的彩虹。我知道他们对这世界仍有话可说,因为他们失去腿脚,却相信恩典。
2010-3-23 写于复活节曁清明节前。
——摘自 灵魂深处闹自由:《与神亲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