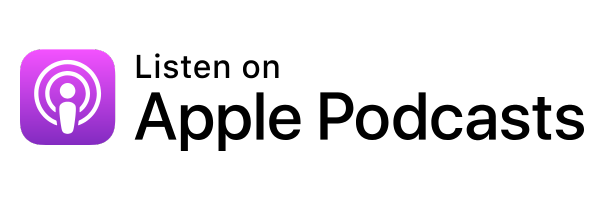2006 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有一部野心勃勃的科幻片《人类之子》(Children of Men),色调灰暗,描写 2027 年人类丧失了繁衍能力,当全球最年轻的一位 18 岁青年死去后,全世界出现了最后一名孕妇。人之子的降临,成为一切惊悚背后的一个眺望。你若为这样一部电影挑公映的日子,是否英雄所见略同,也会放在圣诞节呢。
好像耸人听闻,隔得也太近了些。我们走在街上,不断听见喇叭声响,人只有嫌多的,怎样会嫌少。但若是看另一部电影《被遗忘的天使》,同样在威尼斯电影节上,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意大利外交部联合发起,邀请了全球 7 位著名导演,都有名有姓的,一起拍了这部儿童题材的集锦电影。2007 年陆续在各国上映。电影的全部收入被承诺将用于儿童慈善事业。
片名《All the Invisible Children》(所有被忽略的孩子),在港台翻译为《被遗忘的天使》。其实电影史上有另一部同名的匈牙利电影经典,叙述上世纪 50 年代被苏联入侵后,匈牙利一所孤儿院中发生的故事。那里的孩子渴望一双翅膀,电影中说,“孩子是上帝派来人间的天使”。
当我们一心痛孩子,喜欢把他们称为天使。所以天主教时代的油画,天使都是胖娃娃。还是一个人性的乌托邦,其实挺骄傲的,一个人再没本事,也曾经是一个孩子啊。所以我们档案上的“出身”一栏,都应该填上“天使”,只是该死的生活磨掉了我们的翅膀。那些不被我们看见的孩子,不仅是我们的后代,也是曾经的自己。在斯科特导演的段落中,一位战地摄影记者,回想西非儿童在战乱中的画面,他不可抑制地冲出家去,当他在河边看见幼时同伴在小船上推开波浪,他跳进河中,回到一个孩子的状态。镜头转换成三个孩子,他们一起来到非洲战场,以儿童的目光走过一切废墟。这短片非常棒,将被忽略的孩子这一主题,延伸到了成年人世界。一个会讲故事的导演,总是令写作者的笔羞愧难当。
将儿童看作天使,来自对耶稣一句话的误读。“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接着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但接下来,什么是“小孩子的样式”基督很清楚地给出了寓意,就是“谦卑像这小孩子”。圣经从未将孩子看作圣洁无暇,反而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该死的生活若是该死,该死的源头总在最初的那个人。父母总喜欢把盼望放在孩子身上,以自己的梦想顶替孩子的梦想,以孩子的未来延续自己的未来。因为“我们老了,无所谓了”,他们还年轻。对孩子的偶像化,其实也不是对孩子的,而是自我偶像的一个投射,同时也构成历史主义崇拜的一部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生生不息,真是一个伟大的词语。但生生不息不是我们蒙恩的原因,恰恰是我们蒙救的结果。
《被遗忘的天使》一片,呈现了儿童在当今世界的一个沉重场景,也给了《人类之子》中的危机感一个比科幻更加令人惊悚的注解。每一天,全球有 3 亿多儿童处在饥饿当中,有 1.8 名万儿童将死于饥饿;每一天,全球有 1.2 亿儿童不能上学,有 1200 万艾滋病孤儿,和 230 万儿童艾滋病患者;每一天,有约 70 万的儿童军人挎着 AK47,有 1.32 亿 5 岁至 14 岁的童工在非洲的农场和种植园、缅甸的工地、印度的作坊或中国的黑砖窑工作。2006 年 7 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指出,全世界每一秒钟就有一名 15 岁以下的儿童死于艾滋病。
离 2027 真的很近,离香港导演王家卫的《2046》也很近——这个年份也是一个关于世界末日的著名预言。黑人导演斯派克·李的片段最令我痛心,他描写一个非洲裔的艾滋病少女,段落名叫《基督的孩子在美国》。苦毒、病痛、歧视、咒诅和生命意义的失丧,一切都令人避之不及。艾滋病就像圣经时代的大麻疯,折射出整个世界的罪孽。在这部集锦影片中,无论是身跨卡宾枪、杀人而后自杀的非洲娃娃兵,那不勒斯的街头小流氓,还是塞尔维亚那个不愿离开看守所的小偷,或者吴宇森的镜头中两个贫富悬殊的北京女孩。电影将二十一世纪儿童的苦难呈现在成年人面前。使每一对父母的怀孕计划都面临一次打击。
人类之子,到底为何而来?每一对垂头丧气的夫妻,每一个摇摇欲坠的家庭,都在等待一位天使,结果生下来的还是罪人。于是养狗的就越来越多了,看狗越看越可爱,看人就越来越讨厌。人的位格,成了一个不堪重负的受造物。人将他的盼望,放在低于人的存在之上。山水、自然、物什和猫狗,如同国家、民族、城邦和房屋。就如隔壁的邻居养了一只狗,每次遇见我,就对着狗说,“快叫叔叔好”。我的头一下子就懵了。
有一首著名的圣诞歌曲,叫《这婴孩是谁》。孩子若是我们的拯救,谁是他的拯救?孩子若是天使,我们曾经的翅膀被收拾在哪里?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生命这场戏岂不是背着老板,虚开增值税发票?
这 7 个故事里,你会发现人的尊严和危机与人的多寡没有关系。人不在乎多少,在乎被看见还是被忽视。埃及的法老曾下令杀死全国刚出世的男婴,只剩一个摩西活出生天。晋国的大将军屠岸贾也曾下令杀死全国一岁以下的婴孩,只为了搜捕赵氏孤儿。以色列的大希律王也曾杀死伯利恒全城和四境两岁以下的婴孩,只为了不让弥赛亚来到世间。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当我们失去了孩子,我们还剩下什么呢”。今天似乎没有君王下令,但更多的儿童却当着全世界一一死去。总角之年,已对这个世界伤透了心。程婴为了救赵氏孤儿,甘愿以自己的儿子代死。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怀着信心,甘愿献自己的儿子以撒为祭。但到了最后关口,天使显现,说将有一只无罪的羔羊,代替你的儿子。
没有人没有盼望,真正要紧的不是盼望,而是盼望的由来。《人类之子》的煞尾,借用挪亚方舟的故事,也留下了一丝光明,让观众去举目仰望。来到这世上的,总有一个是替罪羊,如上帝的光闯入黑暗。人类曾经造出来的船,总有一条是方舟。不然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不过是逃上岸的两条鱼,彼此以唾沫求生。
谁可以救谁呢,我们爱,但爱不完全。我们的爱不是那方舟,而是那唾沫。我们称孩子为天使,因为我们已遗忘了天使。
最令人诧异的不是这世界弥漫着罪,而是这世界为什么还不毁灭?有一种被称为“熵”的世界观,以科学主义的和非道德化的方式,将能量耗散所形成的一个负面的量称之为“熵”,所谓世界末日就是熵的最大值。一些科学家认为“熵”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就像我认为罪恶是真实的存在。但“熵”与“罪”的差别在哪里,仍然在一个“位格”的议题内。“熵”不是由一个有情感、有意志、有理性的存在带出来的,因此一个“熵”的世界要么依然构成人定胜天的一部分。即人类以自己的努力可以去调节“熵”值,就像人类凭自己努力可以臻于至善一样。
科学主义与道德主义本就是人性乌托邦的两面。要么这个世界就失去了救赎的可能性,因为“救赎”是位格者之间的关系,来自有位格的创造者的一个情感、意志与智慧的决定,这就是为什么“救赎”的管道最终必须是一个人,和一位道成肉身的上帝。他若不是一个“人”,他与我们有什么相干。我们经历的痛苦、试探和罪的捆绑,实在不足与异类言。他若不是一位“神”。他知道了又有何用。
我也愿为我的亲人死在十字架上,就像总有人愿意跳下河救一个溺水者。但这不是救赎,这叫做大不了一起死。没有位格神,一种世界观譬如“熵”,只是一个自然主义的、物理学的概念。当一个物理概念被当作对宇宙的终极解释时,物理就成了一种自然主义宗教。当人们说“我相信万有引力,我相信进化论,我相信熵的存在”,其实人们并不清楚自己所“信”的到底为何。
1947 年,一群曾参与“曼哈顿计划”(原子核研究)的科学家,设计了一个人类“末日之钟”。这是一个著名的人类危机指数。60 年来,它的指针距离晚上12 点最远的一次,是 1991 年苏东崩溃,时间被调到晚上 11 点 43 分。最近的一次是 1953 年美苏分别研制出氢弹,指针跑到了晚上 11 点 58 分。当我写下这段文字时,人类历史的时间是晚上 11 点 55 分。
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过于物质主义的危机指数。人类是否毁灭,并非那么显要地取决于地球上有多少枚氢弹,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枚氢弹。不如以这两部电影中的孩子,来作为末日之钟的指针吧。世界的毁灭取决于地球上有多少枚失丧的灵魂,多少颗破碎的心,有多少孤儿寡母,多少死亡、怨恨和多少贪得无厌。但世界的尚未毁灭,却单单取决于一位至高者的爱。每一秒钟,这宇宙间若没有一个相反的意志,就是一个圣洁、公义、良善和慈爱的旨意托起这个世界,每一秒钟这世界的毁灭都理所应该。当我察验自己内心的黑暗,我知道这世界不是一个物理的世界,若没有那位托起万有引力的,万有引力就不存在。就算存在,也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说的,“2+2=4 和我有什么相干”,和一个艾滋病孤儿的灵魂又有什么相干。如此我心存感激,知道每一个人原来如此珍贵。我妻子分娩的那个上午,同一间手术室就有十几个婴孩降生。但我仍然庆幸至高者的恒久忍耐,每一秒钟落地的那个孩子,都是人类的最后一个婴孩。每一位孕妇,都是人类的最后一名母亲。
我为这一秒钟感恩,为下一秒钟祈祷。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