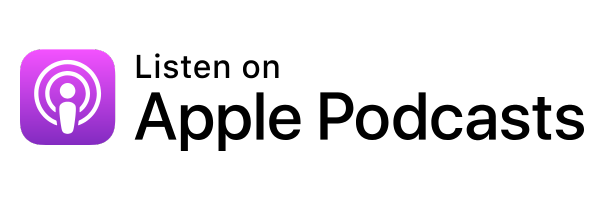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在本周举行的“圣约与世界观:第三届归正神学论坛”上,苏炳森校长的讲座,《基督教古典教育与中国基督教教育的未来》。下面是他的论文,引言部分。我推荐给大家。
王怡牧师,20130802
今年4月在北京召开了基督教教育的研讨会,我在问题回应中提出思考基督教教育首先要面对的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到底要不要基督教教育”,二是“要什么样的基督教教育”。在此,我将着重续谈第二个问题,虽然这两个问题不能截然分开,因为只有具体考虑“要什么样的基督教教育”才可能真正落实对基督教教育总体性质和目标的坚持。第一个问题只是粗糙地说到教育性质上的界限,第二个问题才具体、正面地将此界限竖立起来,并且将其中的内容充实起来。可以说,如果不认真思考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不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而且往往导致在基督教教育的名义下不知不觉地混进过多的世俗教育理念及其做法。
虽然现阶段我们还要花很多精力对家长乃至同工们讲明第一个问题,但从基本的信仰理解来看,第一个问题还是比较清楚的。如果说教育本质上就是信仰的传承,那么基督徒当然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受迦南地的教育。一方面,基督教教育或者说信仰的传承,是上帝美好的旨意和严肃的命令(申6:4-9;诗78:1-8;弗6:4等);另一方面,只有基督教信仰才有可能达到让一个人成为人的根本教育目标;第三方面,教育不但关乎结果,更是关乎过程,教育过程本身也带有敬拜的性质,百科知识的教导、学习和体验要么以封闭的受造界为参照点(各式各样的无神论),要么以上帝为参照点;要么间接地指向自身或其他偶像、要么间接地指向对创造主和救赎主的认识、感恩、爱慕和尊崇。
因此,教育出于上帝(的吩咐)、依靠上帝(的恩典)、归回上帝(的敬拜),就教育性质而言,基督徒进行基督教教育乃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只能是惟一美好的选择。但是,在这惟一选择下我们还得进行更深层次的选择,因为基督教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具体形态在近现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和断裂,使得古典教育模式与现代模式在教育理念、目标和方法等诸多方面尖锐地对立了起来。从而,基督教教育实际的开展将面临这两种模式中非此即彼的选择。在目前中国家庭教会教育的讨论和建立中,一开始就好好面对和思考这一问题,将深刻影响到基督教教育乃至教会本身未来的建造。到底要基督教古典式的教育呢,还是现代的?什么是基督教古典教育?基督教古典教育好像已是个既定事实,那么有没有现代的基督教教育?为此,我们先得稍微考察一下这些教育观念与模式的历史演变。
一、基督教古典教育简史及其在美国的复兴
首先得看看“基督教古典教育”中“古典教育”一词的意味,对这一教育形态的定位,其实可以用其他相近的词来表达,比如“自由教育”、“人文教育”、“博雅教育”等,甚至与最近大学里非常热门的“通识教育”都有重大关系。我们斟酌了很久,最后觉得采用“人文教育”或“古典教育”比较好点,“人文教育”既标示了内容,又体现了跟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清教徒这一重大历史阶段的内在关联,但容易让人联想到“人本主义”或误以为仅仅是现代专业意义上的“人文学科”的学习;“古典教育”凸显了教育的现代性难题,又指出基督教教育两千多年来的宝贵积累,但也容易让人落入狭隘的“古今之争”而非实质性的基督教与非基督教教育之争。但考虑到指出当前教育的“古今之争”正是深刻地思考教育的实质之争(所谓的“雅典与耶路撒冷之争”)的关键路径,最终我们就倾向于采用“基督教古典教育”的提法
基督教古典教育及其潜在的脉络源远流长,上可追溯到犹太人被掳后正式定型的会堂教育,新约时保罗就是在这样严格的训练下成长的;然后是教父们在希腊-罗马文化下的教育实践与主张,这时候基督教开始正式思考基督教与异教文化的关系,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游斯丁、克莱门特、德尔图良、奥利金、杰罗姆、奥古斯丁、卡帕多西亚教父等。德尔图良反对基督教跟希腊文化的结合,但是在他反对的言辞中所采取的思考和修辞方式也深刻地反映了深厚的希腊-罗马文化学养。因而主流的代表是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中对自己曾经迷恋异教文学深表懊悔,但在《论基督教教义》一书中论到基督教与人文学习的关系,提出了“基督教文化宪章”,他也曾经有过系统撰写文法、音乐、辩证、修辞、几何、代数和哲学等艺学科的计划,但是最后只完成《论文法》和《论音乐》两书。奥古斯丁对人文学问既支持又警惕的悖论式立场值得我们深思,这是现今进行基督教古典教育所要处理的重大问题,一方面要看到人文教育(liberal arts,自由教育)某种意义上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更要知道只有福音能让一个人“自由”,即悔改、成圣,达到历世历代教育所宣称的使人成为人的根本目标。
到了中世纪,成型的“七艺”教育体系开始建立,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为了取代异教徒马蒂纳斯·卡佩拉(Capella)的著作《墨丘利与语文学的联姻》(The Marriage of Philology and Mercurius),撰写了《论神圣文献与世俗文献》(Introduction to Religious and Secular Texts),正式将七艺(文法、修辞、逻辑、代数、音乐、几何、天文)与基督教教育联系起来,正式奠定了中世纪七艺的教育体系,直到今天的古典教育都基本上还在这一模式下运行。在七艺中,前三艺(The Trivium,指文法、逻辑、修辞)是基础性的,是学习其他具体学科的基础,而后四艺(The Quadrivium)所代表的专门学科则在不同的时期有所变化和增加。值得注意的是,随着11世纪经院哲学的兴起,三艺中逻辑的教学渐渐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甚至影响到对文法和修辞的理解与运用方式。以逻辑和哲学思辨为重的教育至今还是天主教教育的基本风格和特色,而现代教育片面注重经验,又被实证主义哲学所捆绑,在这方面已经远远无能为力,现今提倡基督教古典教育很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重新恢复深入思考和思辨的智识训练。可以想见,逻辑与智识教育对片面地处于反智倾向、灵恩式思维与说话方式的家庭教会是一个很好的提醒与纠正。
这时期片面突出逻辑训练的风气到了文艺复兴的时候有了很有意味的转变,伊拉斯谟、维夫斯(Vives)等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攻击经院哲学,主张凸显三艺中的修辞,并且将此跟社会改革和对公共事务的关注深刻联系起来。他们将文化主张付诸实践,改变了大学艺科教育的风格,创办了许多人文中学。基督教人文主义接下来大大塑造并继续影响了改教家和清教徒,比如加尔文就明确肯定人文教育的不可或缺:“我们并不拒绝卓越之训练。上帝的圣言固然是所有学问的根基,但人文学(the Liberal Arts)有助于对圣言的充分掌握,故此不能废弃。”随后的清教徒是明确掌握和应用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典范,据说他们迁徙时,随身携带的不单单是圣经和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还有拉丁文语法书和研究古典文学的书籍。改教家和清教徒发展出经典性的整全教义(如《基督教要义》、威斯敏斯特三大准则),并且注重灵修与实践,关注家庭与公共事务,努力建造圣约子民的社会,因此是基督教教育及其目标不可替代的典范,这与其后整个近现代哲学及其教育的世俗化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注重清教徒式的基督教古典人文教育,对目前家庭教会来思考自身处于政治-社会转型关键时期中的历史使命尤有提醒,比如我们深沉的反智倾向,长期在某种错误政治神学的倾向下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基督徒知识分子也往往个人主义化(如对教会委身度不高、忽略家庭建造)和惟理智化(如忽略日常的灵修与实践)等问题。
此后,随着启蒙运动中世俗哲学的兴起及其在教育上的应用(从卢梭到杜威),现今我们这些第一代基督徒非常熟悉的世俗教育形态开始慢慢冲击两千多年来的古典教育,尤其是依附于国家主义成为主导性的教育模式。即便如此,无论中学还是大学,对古典教育的坚持和重提一直没有中断,比如二战后美国许多人在古典教育的主张和实践颇引人注目。由于公立教育的危机和败坏(如暴力、枪杀、毒品、同性恋、文盲反增、教育商业化、家庭的解体、虚假的价值中立……)、共同体凝聚力大大下降这一自由民主社会的固有顽疾等诸多因素,诉诸于共同的西方文明及其价值观来解决公立教育的问题和民族国家竞争力的问题,成了古典教育、自由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复兴的重大原因。当然,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复兴更深层的原因得追溯到“伊甸园之伤”以及近年来新加尔文主义对“基督教世界观”的再次强调。伊甸园之后人类从来就存在着基督教教育与世俗教育、救赎与自义的根本性抗争,只是到了启蒙哲学之后人类社会亮出鲜明的人本主义和无神论立场,这一争斗才明确成为势不两立之态。如果说古典人文哲学因其形式上的真理追求和话语方式后来成为基督真理的载器和表述系统,使得古典文化成为基督教教育本身的必要成分和必然需求,则整个启蒙后的现代文化及其教育,由于鲜明的理性主义、经验实证主义、价值相对主义、科学主义、功利主义、历史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平等主义、个人主义等等基于人本哲学的意识形态,主动成了对抗基督信仰的教育和文化系统。在这个意义上,则不可能有“现代的”基督教教育,只有古典式的基督教教育。
目前美国古典教育脉流众多,总的来说可分为世俗的古典教育与基督教古典教育两种,不过因为都处于反现代的倾向,就有许多相似和重合之处,比如都强调对经典的阅读(推荐的经典也很多是一样的)。世俗古典教育又分为民主式的古典教育与道德式的古典教育,前者的倡导人是阿德勒(Mortimer Adler),他也因编辑了一套西方文明“大书”而著名;后者的代表是西克(David Hicks),他提出一种恢复柏拉图-文艺复兴式的人文主义教育。当然,赫钦斯(Robert Maynard Hutchins)在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和名著教育计划、施特劳斯及其弟子布鲁姆等人寻求的精英式自由教育也在古典教育潮流中影响甚大,可以说这两种大学教育改革的主张分别是民主式的通识教育与精英式的自由教育。有意味的是,他们在中国的效法者分别是最近在中国大学教育改革中颇受争议的甘阳和刘小枫。如果说世俗古典教育中阿德勒民主式的古典教育是亚里士多德式的,而西克的道德式古典教育则是柏拉图式的,则以道格拉斯·威尔森(Douglas Wilson)等人为代表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则可说是奥古斯丁式的。这一发展了30多年的基督教古典教育复兴史对目前我们进行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建构在理论、教材和经验上都有不少的借鉴作用,在这里稍微详细地介绍一下。
在上世纪80年代初,威尔森(Douglas Wilson)在爱达荷州莫斯科小镇开办了一个名叫“逻各斯”(Logos,道)的初级学校,并且在英国著名女作家多萝西·赛耶斯(Dorothy L. Sayers)1947年发表的教育演讲稿“失落之学艺”(The Lost Tools of Learning)中找到了方向,开始在学校推行以“三艺”和基督教世界观为基础的古典人文教育。短短几年中,学校已经因学业水准的突出而在当地颇有名气。1991年,也就是大概办校10年之后,关键的转折点来了,随着教育经验的积累和改革宗视野下深入广泛的思考,威尔森在一系列基督教世界观丛书中发表了《重获失落之学艺》(Recovering the Lost Tools of Learning)一书,书发表后立即引来大量回信咨询如何开办一所基督教古典学校。为此,威尔森不得不号召成立专门机构,结果在1994年“基督教古典学校联盟”(Association of Classical Christian Schools)诞生了,标志着古典教育运动的发展步入了关键性的第二阶段。该机构负责举行年会、开发各种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具体方案、制订独立的标准和资格认证、出版定期的基督教古典教育期刊等事工,目前已有一百多家学校加盟,该联盟甚至有如何开办一家基督教古典学校的全套指南。对我们特别有借鉴意义的是,ACCS里边有三家主要的出版机构提供丰富的古典资源、教育理论与方法、教师培训资源、教材,分别是“逻各斯学校”(Logos School)、正典出版社(Canon Press )和“真理出版社”(Veritas Press)。该运动第三个关键的发展是“新圣安德烈学院”(New St. Andrews College)的成立,该学院提供严格的基督教古典人文的四年本科教育,既解决了基督教古典学校毕业生去处的难题,又反过来培养一些能够从事基督教古典教育的师资,解决了在这方面教师极其稀缺的困难。该学院在古典人文与基督教世界观的视野下进行四年的自由教育(Liberal arts),主要课程安排如下:古典语文及其文学方面,第1年半拉丁文,其后1年半希腊文,第4年可任选拉丁文、希腊文或希伯来文;其他的为,第1年古典修辞学,第2年世界观与生活诸领域,其他学年是世界史尤其是古代史,还有圣经神学、音乐、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