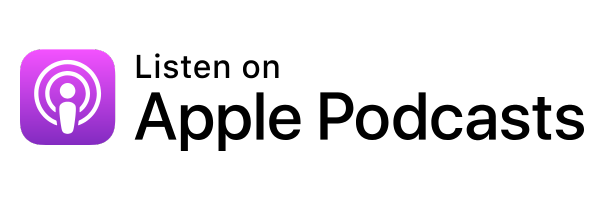引言: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
我刚刚在神学院上完中国教会史课。我先引用一句话,来看基督教的信仰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碰撞。刘晓波在1989年8月出版的《狂妄必遭天责–论中国文化道德沦丧的致命谬误》当中,提出一句很触目惊心的话——“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1989年的悲剧发生的时候,在整个中国社会中,很难听到这样的话,因为,刘晓波本人并不是基督徒。
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到1989年,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在中国文化的主流知识分子的口中,刘晓波思考和面对中国鸦片战争以来100多年屈辱的转折和苦难的历史时,他说出了这样一个命题——“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这是一个否定性的命题,他说“没有”、说“不”, 你会感受到他的情感并不是带着盼望,而是一句悲叹,是在绝望当中的呐喊,是从“89血泊”中所发出来的呐喊。但是,他没有指向对十字架上耶稣宝血的盼望。
所以,无论是刘晓波本人,还是以他为代表的中国200年来的知识分子,以及近几十年来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断地有人归主,但是,从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整体上来讲,对于上帝、对于基督教传到中国,他们的情结仍然是相当地复杂,里面满含了向往、怀疑、痛苦和眼泪等各样的情感。
刘晓波在1989年说出“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的悲剧”这句话,表达了中国文化与基督教来华之间长达千年的纠葛;也表达了宗教改革之后,马礼逊来华200年期间纠缠的关系。让我们来看新教入华以后,英国宣教士麦都斯在1823年用中文写的三字经。他说:“自太初,有上帝。造民物,创天地。无不知,无不在。无不能,真主宰。”从唐朝到马礼逊来华,差不多1200年历史,这是基督教信仰进入中国的一个漫长序曲。在这个序曲中,基督教三度来华,但是,都没有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中扎下根来。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讲,在1807年之前的三度来华中,实际上基督教信仰都没有对中国的文化构成足够的挑战。这些景教的宣教士、天主教的宣教士,都没有勇气,也没有力量,在基督福音的焦点与中国的文化之间构成尖锐的挑战。
实际上,从唐朝贞观年间(公元635年)景教第一次来华,一直到1807年马礼逊来华之前,这1200年的历史,与其说是这些来华的基督教对中国文化构成了挑战,不如说是中国强大的文化对来华的基督教构成了挑战。中国的文化,用柏杨的话说比较难听,叫做“酱缸的文化”;或者用比较好听的话说,叫做“有容乃大”,就是任何东西丢进来,最后都会变成我的一部分。
你看,佛教来了。佛教产生于印度,其本身就是东方文化的一部分,与中国文化之间有很多同质的地方。因此,佛教进来以后,就可以把你“化”进来。而且佛教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也受到了中国道家思想很深的影响。当然,反过来也是有影响的。所以,佛教的异质化程度还不够高。
今天,中国政府提出“基督教中国化”,你不要以为是习近平的突发奇想,或者是他提出的一个对教会的新政策和新态度。实际上,当你去看历史,基督教进入中国的漫长历史是一个失败、拉锯和挣扎的过程,你就知道了一切外来宗教的中国化,实际上都是中国文化以不变应万变,来回应一切外来文化的长达千年的策略和能力。
中国武侠小说中,有一种“化功大法”,无论你是崆峒派,还是武当派,只要你进到我的体内,我都有化功大法,就是把各家各派的内力,都吸到我里面来,我就变成了武林中的高手。不过,这些内力在我里面,还是会导致一些冲突,虽然我把它压在里面,但是,总有一天会崩溃。
到今天为止,我们看见这个“化功大法”似乎还运行得不错。佛教来了,就是佛教的中国化。任何一个外来的宗教,都会经历这个宗教的中国化,那么,基督教也不例外。马礼逊之前的1200年期间,每一次基督教来华,最终都是被“化功大法”化掉了。每一次基督教来华,最终都不是对中国文化构成了尖锐的、决定性的、转折性的挑战,而是受到了中国文化的挑战,被迫妥协、被迫通融,甚至去寻求中国文化的用词来与中国文化交流、共融、融合。
所以,到了新教来华,麦都斯的三字经说:“自太初,有上帝。造民物、创天地。无不知,无不在。无不能,真主宰。”这就是刘晓波所悲叹的——“中国人的悲剧是没有上帝”。
一、从“礼仪之争”到“百年禁教”
那么,我们稍微回顾一下前面的历史。1807年之前,有一个我们称之为百年禁教的时代,就是从康熙的时候开始的。1793年,英国特使马戛尔尼来华,比马礼逊还早一点,不过,他来华不是代表教会,而是代表英国来朝贺乾隆80大寿。这是中国传统,叫做天朝的朝贡体制——万国来朝。马戛尔尼带来了很多的礼物来朝贺,同时也提出希望能够通商——就是鸦片战争之后的“五口通商”。
乾隆很高兴啊:在那么遥远的地方都有人知道我,在那么遥远的地方都有人来朝贺我们天朝,而且还想和我们通商,这也是很开心的事,是可以答应的。但是,发生了一件外交上礼仪之争的事件。中国人说:你见皇帝,咱们的礼仪是要三跪九叩。马戛尔尼说:这个不行,绝对不可以。我代表一个国家,我是国家的公使,我不能够在另一个国家面前下拜。中国人说:这是中国传统的朝拜体制,我们必须当你是天远的附属之国或者番邦来见天朝。但是,马戛尔尼说:不,我们是平等国家之间的交往。我们是敬拜上帝的,我们是不跪人的,我们连父母都不跪的,我们自己的君王也不跪的。第一,我代表我的君王,我的君王不能来跪你的君王。第二,我在我自己的君王面前,我都不跪,都不会用这个礼仪。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就有一个基督教文明带给中国文化难以接受的根本观点,就是敬拜上帝还是敬拜皇帝的问题。如果有一位上帝,就意味着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在上帝面前虽然也有尊卑,也有在上和在下的差别,在下的仍然要尊敬或者顺服在上的,但是,在上帝的面前,这种人间的差序格局却不再是绝对的,而是具有平等和尊贵的位置。
那么,这个反映在基本礼仪上面的观念,就与中国文化中的那个根深蒂固的对人的敬拜——对皇帝的那种崇拜——构成了尖锐的冲突。在这一点上,你会看见,英国的公使来华无非就是做生意嘛,就是赚钱嘛。如果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只要你跪,那么万国的荣华就给你嘛。但是,马戛尔尼说:我不干,这个是绝对不可以的事。于是,乾隆皇帝就说:那你回去吧。我们天朝地大物博,什么都不缺,我们不需要与你做生意。结果,马戛尔尼就空手而返。
这是中西交流的一个失败。这个失败和基督教信仰还没有很直接的关系,但是,仍然触及到了基督教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本质冲突。如果你说,人主要是看重利益的,那么,你会看到乾隆和马戛尔尼在这件事情上,按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太意气用事了!太意气用事了,生意第一嘛,谁和钱过不去呢?无非就是跪拜嘛,不跪就算了,这是从这边(乾隆)来讲;或者从那边(马戛尔尼)来讲,跪就跪嘛。但是,在这个决裂中,你看到中国文化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与基督教文明里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东西,似乎有着非此即彼的冲突。
如果一个英国的公使过来和中国皇帝打交道的时候,因为跪拜而决裂了,那么,我们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再往前,从利玛窦开始,那些天主教的传教士在中国是怎么活下来的呢?他们是怎么在朝廷为官的呢?是他们已经成功地对中国的帝王崇拜构成了足够的挑战吗?不是,而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妥协。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人家一个公使在这个问题上,都可以把国家的利益和经济的利益放在一边——不跪就是不跪,回去就回去!但是,教会的宣教士却有太多的妥协。
当时,礼仪之争还没有发生在国家的层面,而是发生在民间生活的层面,就是关于祭祖和祭孔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的基督徒,如果信了耶稣,相信了“太初有上帝,独一的真神”,那么,他将怎么面对他家族里面的祖先崇拜呢?在私人生活中是祖先的崇拜,在政治生活中是帝王的崇拜,在文化生活中是孔子的崇拜。按照中国传统来讲,就是有一个政统(政治的正确性与权威性)和道统(道德的正确性和权威性)的体系。在道德的层面、文化的层面,是跪拜孔子;在政治的层面,是跪拜皇帝;在私人生活的层面,是跪拜祖先。
所以,这是整个中国文化的核心,体现为三个层面的跪拜:私人的层面、文化的层面和国家的层面。礼仪之争,其实还没有发生在国家层面。如果天主教的宣教士够有骨气的话,第一年就应该像马戛尔尼一样,与中国的皇帝发生非此即彼的、非伤即死的冲突。但是,天主教的宣教士在这个时期回避了这个冲突,所以,从来没有在国家层面发生关于帝王敬拜的冲突。
不过,慢慢地,因为信耶稣的人——天主教徒也慢慢地多起来,有士大夫,也有一些普通的人,他们每一天、每一年都要面对家族日常生活层面的冲突——祭拜祖先。你知道,就算是到了200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国的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乡村,一个人信了主,在这个层面与家族的冲突仍然非常地尖锐。
清明节,你怎么办?家里人要烧香,你怎么办?家里人要祭祖,你怎么办?家里有祖先、去世亲人的牌位,你怎么办?过年了,让你来点一根香、放一排祭品,你怎么办?直到今天还这样,那你就可以想象,200年前的冲突是多么地尖锐。因此,利玛窦,包括整个天主教的耶稣会都采取了一种通融的态度,就是这些不算敬拜,不算拜偶像,不算违背上帝的律法,不算违背十诫的第一、第二条戒律,所以,他们允许中国的基督徒可以参与祭祖和祭孔的仪式。
前段时间,我读到法国的帕斯卡尔在《致外省人信札》这本书里对耶稣会的批评。他虽然没有来过中国,不过他听到了,他在书里讽刺了这种基督教中国化的走向。因着宗教改革的冲击,在天主教的内部也有好几波不同的、我们总体上称为反宗教改革的宗教改革,也有对天主教内部的改革,包括在信仰上的一些刺激。在这些刺激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接近新教信仰的教派,叫做杨森派。杨森派被称为天主教内的一次回归奥古斯丁的恩典教育的运动。所以,也有很多历史学家说,杨森派好像是天主教会内部的加尔文主义者。但是,他们没有发展起来,大概二三十年的时间,就被法国的国王和罗马的教宗联合剿灭了,有些人被杀头了,有些修道院被关了。
帕斯卡尔作为一个思想家,也是一个科学家,当时是杨森派的一个重要的神学上的发言人。他的《致外省人信札》是用那个时代比较常用的书信方式写的,其实是一个论辩集,是杨森派用来与耶稣会所代表的天主教传统教义进行争辩的。在争辩中,他用到一个例子,他说,天主教有一个很强的,我们今天叫做道德主义或者叫做功德的称义观。所以,他们在中国,他们在印度(他没有提到日本,其实都差不多),他们在那里发展出来一种什么样的宣教策略呢?就是如果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哪个国家的文化中是被藐视的,他们就会在那里回避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只传扬一位荣耀的上帝以及西方文明的科学和知识。
我觉得帕斯卡尔的这一断言和评论,基本上可以总结从景教到18世纪马礼逊来华之前基督教入华的历史。甚至他还提到一个非常令人讽刺的事情,他说,听说他们在中国是这样做的——他们如此诡诈地教导中国的基督徒,将一个耶稣的十字架悄悄地放在里面的衣服中,然后再去参加祭孔的仪式,就会在内心把敬拜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话说得很刻薄,但是说得很真实。换言之,如果换成一句中国的话,就是“酒肉穿肠过,基督心中留”。这是帕斯卡尔对当时的一个评价。那么到了1720年,为什么会产生出礼仪之争呢?因为之前天主教来华的宣教声音,都是被耶稣会垄断的,其他的修会不能来。到了那个时候,其他的修会如道明会,还有其他的一些人都来了。当然,耶稣会的研究者说,他们来了有点嫉妒耶稣会的成就,想要抢占这个传教市场。这是修会之间、罪人之间的争夺。
但是,这些道明会,还有其他的修会来到之后,他们在信仰上更加保守。当然,耶稣会就说:你们刚刚来,你们还不懂啊。你们不知道中国的文化,你们不知道不这样做的话,基督教在中国是根本站不稳的,是一定会被赶出去的!你们刚刚来,你们血气方刚,你们瞧不起前辈的工作,你们就在那里指指点点。
道明会的这些人一来就说:不行,一个基督徒绝对不可以这样!十诫是非常清楚的。中国是一个敬拜人的文化,敬拜孔子、敬拜皇帝、祭拜祖先,与基督教的信仰之间是绝对不能两立的!所以,如果一个人归信基督,就应该弃绝这样的敬拜。耶稣会对此回答说:开玩笑!你只知道读书,你不知道中国的处境是什么!如果这样,还传什么福音呢?如果这样,不是全部都被杀头了?
这些道明会的人,就到梵蒂冈去告耶稣会在中国乱搞。然后,梵蒂冈进行了调查,开了会,最后教宗下了一个命令:祭孔、祭祖,虽然还没有提到跪拜皇帝、没有提到国家政治层面,还只是在文化与生活的层面,但是,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与基督教的信仰直接冲突的。归信耶稣的中国人,就应当弃绝祭孔和祭祖。
教宗就派了一个公使,将这个命令传达到中国。当时是康熙皇帝,康熙和乾隆一样,就大怒了——你爱来不来!听说康熙还写过几首基督教的诗,所以,耶稣会的人就说,本来康熙都要皈主了;康熙一旦皈主,中国就是一个基督教王国了!康熙都是慕道友了,差一脚就要进了!结果教宗禁令这样一来,康熙就下令禁教,把所有的宣教士赶出去了。由此,闭关锁国100年!
康熙那个时候,虽然下了命令,但是执行还不是那么严格。雍正上台之后,执行就非常严了——凡华人信教者,一律处斩。所以,我们称为“禁教百年”。从1720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到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然后沿海才有五口通商;宣教士才合法地进来,可以在沿海五个地方建立会堂。这期间大概是120年时间。中国闭关锁国,将整个基督教和西方社会完全地赶出国门,长达120年的时间。
二、新教以非法和卑微的方式进入中国
你就知道,马礼逊来华是在这120年中间,是禁教期间来华的。这个也很有意思,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挑战,从景教来华一直到元朝的也力可温教,一直到明朝的耶稣会来华,都受到国家级别的高规格待遇。一般都是在钓鱼台吃饭,一般都是在中南海开会,一般都是在午门外接见,一般都是由副总理级别迎接。甚至景教来华的时候,是宰相房玄龄亲自地到郊外,迎接阿罗本进入长安城——这是总理级别的待遇。
基督教前几次来华,都是合法的,而且都是高级别的待遇,都与官方有蛮好的关系,而且这些宣教士也都致力于与皇室之间建立很好的关系。皇室给了他们很高的待遇,比如说阿罗本,就是景教来华的宣教士,被唐太宗册封为护国大法王。这相当于今天的全国政协副主席,级别是很高的。但是,每一次来华都是北上,去到都城,要集中在皇帝的身上,而没有对中国文化构成挑战。当然,对此我会讲到一些例子和典籍。
可是,当马礼逊来华的时候,是非法的。马礼逊来华建立的教会是家庭教会。马礼逊来华是非法的,他上岸就是非法的,他要来学中文是非法的,他要来传福音更是非法的,他要来翻译、出版圣经更是非法的。总之,马礼逊来华,从头到尾都是非法的。这与我们今天的家庭教会一样,从头到尾都非法。
我们感谢主的是,当时,基督教信仰的十字架焦点,对一神论所带来的对中国文化的偶像崇拜以及在文化层面上对中国文化的道德自义,构成的最尖锐的挑战,是通过非法状态、是通过卑微的道路进行的。
这有点像保罗去罗马。不过,西方宣教士来到中国和当年保罗去到罗马,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其实导致了非常复杂的基督教与中国的关系。保罗去到罗马的时候,他是把真理带到那里去,告诉他们说:噢,你们不知道真理,我来告诉你们真理。你们有一位未识的神,不知道他是谁,我来告诉你们——他是“太初有上帝”的那一位神。
但是,保罗是从一个文化和政治都边缘、落后的地区,就是耶路撒冷犹太地,去到罗马,就是全世界最繁华的地方,就是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文化的中心,也就是这个全世界敬拜的中心。所以,这是一个弱势的文化,向着一个强势的文化传福音。弱势文化向着强势文化传福音,所传扬的福音本身又是一位降卑的耶稣基督,他以苦弱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彰显一种被这个世界看为是无能的真正的能力、被这个世界看为是愚拙的真正的智慧。因为,罗马人认为他比你聪明,罗马人认为他比你有能力。你是一个完全在人家面前无能的人,然后正好也向他传一个无能的能力;你正好在人家面前是一个卑微的、被人家看为是愚拙的人,非得向人家传扬一个被看为是愚拙的真正的智慧。所以,这个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福音传扬,正好与这个福音的实质相对应,就是这种福音的实质是卑微、是十字架的道路。因此,保罗到罗马的方式是怎么去的呢?他是被罗马士兵护送去的,他自身是处于非法状态的,他是被押去的,他是带着镣铐去的。福音,是带着镣铐进入罗马的。
福音高于一切地上万族万国的文化。真正力量的彰显就是——福音常常是带着镣铐的。福音是带着卑微的样式进入到一个优势的、高傲的文化中,以十字架的方式来构成对那个文化的挑战。保罗就是用这种方式把福音带到罗马的。
我们回过头来看中国,从景教一直到天主教的耶稣会,他们不是这样的。西方向中国传福音有一个很大的艰难,是反过来的艰难,就是他们是优势文化向着劣势文化传福音。向你传福音的那个人,本来就比你能干。他是有能力的,向你们这些无能的人传福音;他是聪明的、有智慧的,向你们这些愚拙的人传福音;他是文明的,向你们这些野蛮的人传福音;他是开放的,向你们封闭的人传福音。
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就带着一个文化上的样式。这个样式,老实说就是太漂亮了、太体面了!所以,当利玛窦来到中国的时候,他来传“有一位上帝”。但是,中国人说,哦,有一位上帝,这个我不是很在乎,但是,那个布谷布谷的自鸣钟,太奇妙了!然后,利玛窦又带来一张世界地图。哇,世界地图,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我们太愚昧了,我们真的是太愚昧了!
所以,当你没有去认识福音之前,你首先就认识了天文、历法。哇,人家老外算的历法就是准,我们以前的历法都算错了!哇,他们各个方面,包括所有的学问,都比我们强!他们代表的是一个优势的文明。
让我们这样讲,有很多人说,今天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与北美华人基督徒有一个很大的区别——这话不是我们讲的,是北美的华人自己讲的——他们说:在我们北美,我们是坐着花轿进天堂的;在中国,他们是背着十字架进天堂的。
那么,福音来到中国,在马礼逊来华之前的1200年期间,基督教都是坐着花轿进入中国的。基督教来到中国,都带着一连串的陪嫁,带着好多的陪嫁。你知道,富裕人家的女子出嫁,除了把这个女子给你,还要给你好大一堆东西。有的时候,很多人是因为那堆东西,才娶这个女子的。穷苦人家除了这个女子,其他什么都没有;除非你是真要这个女子,因为除了这个女子,其他也没什么好要的。
有的时候,如果陪嫁太多的话,就会有一个麻烦。麻烦就是,你到底爱不爱我?麻烦就是,你到底爱我呢,还是爱我们娘家的这些东西?所以,当福音传到中国来,它带了太多的陪嫁来,它带着整个西方的文明,它带着那一切的优越感、一切的成就,使得福音不是以一种卑微的方式来进入的。
可是,到了马礼逊的时候,有了一个翻转。从马礼逊之后的福音来华,不再是向北、向北、再向北。北,代表着帝王所在。从马礼逊来华,特别再到后来的戴德生,你就看到,新教在中国是向西、向西、再向西,是不断地往内地走,不断地往边缘走,不断地往底层走,不断地扎根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而不是把焦点放在攻下中南海、把焦点放在让皇帝信主。 你怎么让皇帝信主呢?除非皇帝逃难的时候,否则的话,你就要带一大批嫁妆,才能够进去给皇帝传福音。
所以,当新教的马礼逊来华的时候,他是以一个罪犯的身份来华的,因为他一上岸就是偷渡客。为什么20年后,他要被迫地加入东印度公司,在那里得到一个翻译的职位呢?因为,只有东印度公司当时取得了特许的进入中国的合法身份,他才摆脱了偷渡客的罪犯身份。
三、中国文化敬拜的核心是人、国家和权力
刘晓波说中国人没有上帝。新教的宣教士一来,就把上帝的圣经以中国传统的三字经方式告诉你——“自太初,有上帝”。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传统中的上帝。
什么是中国文化?这个问题太大了,但是,有一个最根本的,就是任何一种文化的核心,一定是与神的关系。任何一种文化的核心,一定都是关于这个文化中的敬拜。我想指出一点,就是任何一种文化,当中最核心的部分是人与上帝的关系。为什么?因为人是按着神的形像所造的,人的里面一定有敬拜的渴望。人一旦形成了一个群体、国家,一旦发展出一种文化,这个文化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他在这种文化中对上帝的认识,包括对上帝的错误认识。
我这里说的上帝,不是说圣灵所启示的那一位上帝,就在中国文化中。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独一的上帝。所以,在任何一种文化中,只要人里面有神的形象,人就一定会去回应、去渴慕、去揣摩、去认识那一位独一的上帝。任何一种文化的特征,都是基于对所认识的那一位上帝之间的关系,以及因此建立起来的敬拜。这就是这个文化的核心。
从这样的角度,我们来看中国传统中的上帝。虽然中国的典籍中有“上帝”这两个字——“昊天上帝”,但是,实际上什么是中国传统中的“上帝”呢?什么是中国文化中核心的人与神呢?或者用中国的话说,人与天之间的那个关系,是基于中国人对天的关系所建立起来的敬拜。
没有敬拜,就没有文化共同体;没有敬拜,就没有政治共同体。任何的一种统治,一定建立在敬拜的基础上;任何一个文化的共同体,一定建立在人与天,或者人与神的关系上面。
那么,针对这个关系,我讲三点。我认为,整个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什么是它的神?我们不是来问,中国典籍中有没有圣经中的上帝?我觉得这个问法本身就是一个陷阱。所以,我们真正地来问一个问题,就好像我们对一位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向他说:你要信神,你要信真的神,你不能拜偶像。那位朋友可能对你说:我不信,我什么都不信;我也不烧香拜佛,我也不信你们那个基督教的上帝,我什么都不信。然后,我们就对他说:不。你一定是信什么的!按照圣经,人要么是敬拜独一的真神,要么是敬拜假神。真正的问题,不是你什么都不信;真正的问题,是让我们来谈一谈你生命中的神是什么。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他的神、都有他的敬拜,而这些在圣经中被视为——偶像崇拜。
所以,当我们对慕道友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需要和他一起或者帮助他来找出他生命中的偶像是什么。个人生命和国家生活一样,都是建立在敬拜之上的。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到现在为止,你既然没有相信耶稣、你既然没有相信圣经启示的那一位上帝,那么,什么是你现在生命中的敬拜?你在拜什么?你是拜你妈还是拜你女儿?你是拜钱还是拜官?你肯定有拜的东西,我们要找出你生命中的假神来!
面对中国文化的时候,也是一样,最重要的不是那些典籍当中出现的“上帝”两个字,到底是不是圣经中所讲的上帝,而是说中国文化中的那个假神是什么?中国文化核心里面的那个敬拜是什么?
1、以人为帝
第一,是以人为帝。很多时候,我们有提到上帝,但是,其实在古代的典籍中,提到“上帝”这两个字连在一起的地方并不太多。如果只提到“帝”,不加“上”,那么,“帝”在中国远古的典籍中次数是更多的。在远古的时候,那个“帝”不是指“皇帝”,而是指“上帝”,就是指神。“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与我何有哉?”这里的“帝”,是指到天,是指到上帝。所以,在中国的远古典籍中,说“帝”还是说“上帝”,其实都是在指他们所认识的那一个朦胧中的神。
因此来讲,重要的一点就是,先秦的文化到了秦朝的时候,就开始以人为帝。以人为帝,其实就是以人为神。在儒家的传统中,将人以帝,以天子,甚至以帝为圣。儒家所讲的圣人,真正的圣人,或者最大的圣人,是什么呢?不是知识分子,不是孔子,而是帝王。
中国儒家传统中,真正的至圣是谁呀?尧舜禹,直到周文王。“文王拘而演《周易》”,文王带来中国儒家传统的一个词,与“政教合一”比较类似,叫做“君师合一”。所以,在中国儒家传统中,“帝”代表着政教合一,就是精神权威的祭司和政治意义上的君王领袖,是合为一体的。 所以,中国的皇帝与欧洲的君王,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欧洲的君王,就叫君王。君王就是政治意义上的领袖,是王的意思。但是,在欧洲从来没有君师合一的君王概念。 如果君师合一了,就叫皇帝。如果君师合一了,用今天的话讲,就叫国家主席兼中共中央总书记。
中国几千年以来,直到今天,这是最根本的东西,从周文王到习近平是一脉相承的。习近平最大的梦想,不过就是做周文王而已,就是做中国文化的复兴。他的典范就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那个系统,就是政教合一、君师合一、以人为帝、以帝为圣。真正的大圣人一定是王,真正的大儒乃是三公。古代的三公,相当于现在的政协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三公乃是大儒,这是儒家一直以来的传统。对于上帝这个词,余英时先生在考证里说,上帝在中国的典籍里,并不代表一个具有人格化位格的独一神,实际上它只不过是在泛神的文化中,特别地指向帝王的神圣来源。也就是说,地上如果有个人是皇帝,那么,皇帝的祖先是谁呢?皇帝的祖先,当然是血缘上的祖先,往上数,数到最后,还不就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皇帝的权威性、神圣性是从哪里来的呢?如果皇帝的祖先不过和你我的祖先一样——以前都是一起要饭的,那么,为什么他是皇帝了呢?大家以前一起要饭,为什么他的后代就是皇帝了呢?
所以,中国的皇帝是一个宗教概念,这个就是我说的中国的皇帝和西方的君王截然不同的地方。皇帝本身是一个敬拜的概念,是一个宗教的概念,他一定有神圣的来源。皇帝一定有一个神圣的、从天而来的来源,而不只是从肉身推到一个乞丐。那么,这一个来源,就是上帝。
实际上,就古代的中国来讲,家家户户都有家神。你家都有祖先的敬拜,你家都有家祭。那么,皇帝也有他的家祭,他的家祭就是祭上帝。所以,让我这样讲,最初上帝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只不过是人间帝王的一个家神。上帝是皇帝家的神,与你何干?根本和你没关系!
但是,与你建立关系的是这个皇帝。或者可以这样讲,在中国的那个崇拜系统中,地上的那个皇帝,是你与那个遥远的上帝之间的中保。他是通过这个中保来治理和统治的,你也是通过这个中保来敬拜那一位上帝的。所以,中国古代的上帝,从来就不是我们每个人的上帝。我们每个人生活中真实的上帝,是皇帝。他是天子,只有他可以祭天。在中国的古代,如果有人敢祭天,那就是谋反。你说,今天过年,咱们祭一下咱们王家的列祖列宗吧。这个是合法的,对吧?你说,今天过年,咱们祭一下那个上天——“昊天上帝”吧。这个就得满门抄斩。“昊天上帝”是你能祭的吗?你姓赵吗?你不姓赵,这神就和你没关系!
所以,皇帝在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其实是一个中保。如果有一位遥远的中国的神,那么,皇帝才是那个中保。因为帝王在地上是高于世人的,所以,上帝也是高于诸神的。因此,上帝只不过是泛神的文化中,特别地指向君王崇拜的一个概念而已。
2、以国为天
第二,就是以国为天。 我们提到天朝的心态,天朝的体制。老实说,前几天我在教中国教会史课,人们一定会提到关于宣教士在鸦片战争之后所谓的“不平等条约”中的作用问题。但是,我一直比较反对这个说法,因为我认为,南京条约是中国和其他国家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而不是不平等条约。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平等条约,因为就像马戛尔尼和乾隆一样。人家大英帝国,也不是后妈养的;人家大英帝国也是在全世界响当当的;人家到你这里来,想和你平等一下——咱们是平等关系啊。你说:去去去,谁跟你平等!中国传统的天朝观念下,没有平等的观念。这是天朝与番邦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天朝的皇帝如果是天的代表,那么,谁跟你玩平等的游戏啊!
实际上,鸦片战争迫使清政府承认自己是万族当中的一族,是万国当中的一国,并且只能够作为战败国,来与其他国家签订一个平等条约。在中国历史上,从孙中山、毛泽东开始讲不平等条约,他们所讲的不平等,是指到内容上对我不平等,因为——你割地赔款嘛。但是,实际上,在欧洲的历史中,所有的国际平等条约中,战败国一定是割地赔款,不会因为内容上是割地赔款,就说这个条约本身是不平等条约。明白这个意思吗?
因为,如果他们仍然处在不平等中,就根本没有条约。你看中国古代,如果我们打赢了,谁和战败国签条约?直接把你妈卖了,把你女儿送到官窑里去;把你们家抢了,然后再把你放在监狱中,过二十年能够把你特赦出来,就算是好的了。
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中,根本就没有和战败的人签条约的观念。你战败了,你就是我的,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怎么可能有条约呢?你都打败了,生死都要由我宰割!条约,是建立在平等主体之间的。所以,人家打赢了你,然后想和你签条约,这是从来没有的事。咱们以前打赢了别人,也没有签条约。而且,咱们要是没有把他们打败,也绝不和他们签条约,因为咱们是天朝!
实际上,南京条约意味着,这是中国进入现代平等的主权国家行列中的第一次平等条约。至于割地赔款,那是战败本身的结果,而不是代表这个条约的平等关系。为什么你不接受它呢?因为你是天朝的体制,除了以皇帝、以人为帝,以国为天,这是一种对国家和民族的神话。这个神话,从中国古代的秦开始,一直到今天的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际上,今天你看共产党,要提的也不是共产主义了,它都不好意思讲共产主义的伟大复兴了。对吧?它脸皮都没那么厚了,现在,它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所以,整个国族的神话,古代的帝王崇拜和现在的国家崇拜的结合,是中国文化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迄今为止,我们可以这样讲,基督教尚未动摇这个核心,尚未动摇中国文化最核心的这个部分。
但是,上帝借着60多年来的家庭教会,上帝借着马礼逊卑微的方式,向中国传福音,开始了这一个动摇的过程。之前的1200年,基督教都没有真正地对中国文化最核心的部分开始进行挑战。从马礼逊来华,从戴德生卑微地向西宣教,从中国教会1900年庚子事变的受难,从中国家庭教会60多年来的受逼迫和受苦的过程中,这样的挑战才开始进行。如果我们持续地受苦,并且在受苦中无法被连根拔起来,而是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之中,那么,我们就会对中国文化中的这个最根深蒂固的核心,开始构成挑战。
实际上,今天的中国社会,能够对这个古代的帝王崇拜与现代的国家崇拜相结合的中国文化的核心——这一个肿瘤,构成挑战的,唯有家庭教会,当然,也包括天主教会的地下教会,就是广义上的基督教。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只有基督教构成了挑战。知识分子,从来没有对它构成挑战;民间团体,从来没有对它构成挑战;其他被中国化的外来宗教,从来没有对它构成挑战;儒家或者中国文化内部的变革和更新,也从来没有对它构成挑战。
3、以权为神
第三,以权为神。帝王崇拜和国家崇拜的必然产物,就是权力崇拜,就是以权为神。 在中国,对皇帝、国家、权力这三个的崇拜,就是根深蒂固地辖制每一个中国人灵魂和生命的文化DNA。 这个文化DNA,在真正认识耶稣基督的重生得救的人那里,开始被破掉,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去看自己,我们都会说——破得还不够,在我们的生命中破得还不够。那么,上帝借着这一些重生得救的他的儿女,对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上的破除,也还远远不够,但是,这已经开始构成了对中国文化核心的最尖锐的挑战。
所以,我讲中国文化的核心,从人与神的关系——就是从中国人对神的认识,以及因此建立起来的敬拜来看,2000年文化的核心,用一句话概括——2000年,制制皆秦制也。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是政教合一的国家主义与皇权专制。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你就会对中国的文化过于美化。当然,往下的层面去看,儒家有没有一些在伦理方面美好的地方?道家的思想有没有比较高超的部分?然后再到器物的层面,再到制度的层面,或者再到文学和审美的层面,有没有美好的地方?当然都有,当然都有!
这个民族一定是有上帝的普遍恩惠在其中的,但是,上面的概括,才是它的核心。就好像该隐犯罪之后被驱逐,他的后代开始建立了第一座城以诺。那里的文化繁不繁荣呢?吹拉弹唱,什么都有;建筑、艺术、美术,什么都有。但是,因为这个文化的实质,是传扬人的名,是抵挡对上帝的敬拜,是以他们自己的骄傲为神,是以自己为神,所以,神彻底地摧毁了它!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模式,就是今天共产党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与一党专制。从这一点来讲,一千四百年来,中国没有变过!如果你看文化的其他层面,请问:今天的中国文化和一千四百年前的中国的每一个层面,是不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当然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左到右,从前到后,简直是无法想象的变化!但是,我们看到,那个文化里的核心,其实是一成不变!
如果看不到那一个一成不变,你就会高看了那一个欣欣向荣的变化、那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你的整个的生命,就没有办法归回到对独一上帝的敬拜;你的整个的生命的实质,就没有办法归回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恩典的统治。这个恩典的统治,首先征服你这个个人,然后通过教会,也慢慢地通过上帝大能的手,掌管人类历史和中国历史。
四、中国文化始终把基督教视为异端
让我举两个例子。根据《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基督教在大约1400年前,唐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就已经来到中国。我举碑中的几句原话:“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碑文说,因为景教得到了皇帝的支持,所以一下子传播得很厉害——因为有政府的支持,马上就 “寺满百城,法流十道”。包括当时的成都,也是景教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在城西有很高很辉煌的大秦寺,就是景教的寺庙。但是,景教慢慢地就产生了文化的冲突,这里记载的就是与佛教和儒教的冲突。 “释子用壮”,“释子”是指佛家的和尚。“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西镐”中,“先天末”是公元713年,而“东周”与“西镐”指的是什么呢?你知道,在中国古代,这就是指洛阳和长安(西安)。洛阳和西安在今天来讲,就是像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大城市。这个地方引用到中国的传统典籍《论语》,“下士”是指儒家,这里当然是对儒家藐视的提法。因为《论语》中说,“上士闻道,就勤而行之。”就是上士听到道以后,就说我要去行啊。“中士闻道,若有若存。”中士听道后说,好好好,知道了,我还有事,也不说是也不说非,总之,与我没什么关系。 下士闻道呢,就哈哈大笑,就嘲讽你。
所以,到了“先天末”的时候,儒家的人就起来攻击景教的教义,就开始嘲笑、诽谤和藐视,所以叫“下士大笑”。“释子用壮”,这是《易经》中的一句话,叫做“君子用罔,小人用壮”。“小人用壮”的意思,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叫做君子动口不动手,小人动手不动口。小人说不赢了,就开始骂了。持强就是这个意思,持强不一定是真动手,也包括气势上骂人,总之,就是血气上来了,他就不好好和你谈。
所以,碑文在这里说,景教来华仅仅几十年的时间,就引起了和佛儒之间的冲突。佛儒就联合起来,在中国最大的两个城市诽谤、攻击景教。基督教在中国1400年了,其实都被视为是中国文化的异端。
今天,我们中国有“邪教”这个词,法律上有“邪教罪”。在中国古代,当然最常见的邪教,广义上来讲就是白莲教。有时候学者用这个白莲教,来指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一切被视为非法的各种民间宗教的名称。
中国以儒教为正统,那么,在民间就有非法的邪教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也就叫做白莲教系统。历朝历代很多农民起来革命的时候,都是白莲教系统。为什么呢?中国古代的所有农民革命,一定是宗教性的。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是宗教性的,帝王崇拜和帝王统治本身就是宗教性的。所以,你如果要打败他,要改朝换代,也一定是宗教性的。没有宗教性,你不可能改朝换代。刚才我们不是说过,你不能祭天吗?所以,对农民革命来说,咱们今天祭天,那就表明造反了。因为你开始祭天,就表明你要改朝换代。改朝换代就是造反,天子就这样变换的。
所以,从康熙到雍正禁教的时候,就开始发展出一个概念,叫做“邪教”。而那个时候的邪教,是指天主教,也就是基督教。“我中华正教也”,有邪教就有正教。所以,今天我们来问,为什么说以邪教罪来打压宗教,是违反宗教信仰自由的呢?作为中国的政府,你凭什么说人家“邪”呢?有邪教就有正教,那中国的宗教是什么呢?就是它自己嘛!它只有以自己为正教,它才能来定邪教嘛。
中国1400年来,都是以儒家文明为正教,所以,太平天国起来的时候,或者雍正开始禁教的时候,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叫“护教”。我们今天教会要讲护教学,但是,中国从康熙以来一直到今天,也在讲“护教学”,今天共产党员讲“护教”的用语叫“保卫国家意识形态安全”。
中国100多年来,甚至是1400年来,自己本身都是宗教性的,所以,它一定都有护教的意思,它要将它的正统之外的宗教都定为邪教。因此,基督教与佛儒之争持续了1400年时间。义和团运动完全是民间宗教和白莲教、佛教的民间形态的一个大融合。到了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也是知识分子的一个大融合。然后,到前些年新儒家起来,包括北京大学10个博士联名,他们都要抵制基督教,抵制圣诞节。在这里,你都会看到这一个1400年以来的异端与正统之争。
再看碑文的一段话,就更有意思了。这里讲到天宝初(公元742年),就是唐玄宗的时候。“天宝初,令大将军髙力士,送五圣写真,寺内安置;赐绢百疋,奉庆睿图。龙髯虽逺,弓剑可攀;日角舒光,天颜咫尺。”这个,就是(今天中国政府)“五进五化”的开始;这个,就是基督教中国化的开始。
自从景教来华,基督教就一直是三自爱国教会,你明白吗?三自爱国教会不是从共产党才开始的,共产党也是被中国文化核心所塑造的,虽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外来的,但是,共产党都是中国人嘛,对不对?哪个共产党员不是中国人啊?整个共产党,实际上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产物,并不单单只有马列的意识形态,那个是披在身上的一件外衣。
所以,三自教会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他们建了景教的寺庙,然后就叫大将军高力士(什么大将军,不过就是个太监),然后将“五圣写真”送去。我刚才讲,圣是什么?圣就是皇帝。皇帝为圣,这就是中国最核心的文化的敬拜。那么,“五圣”是什么意思呢?是从李渊开始到那个时候的五个皇帝。不但现在活着的,连死了的都来了。你们年龄大的,你们都知道这件事吧——马恩列斯毛,“五圣写真”是不是这样子的呢?我们几十年都是这样过来的,现在就好多地方都开始挂习近平的像了,现在开始要将红旗插进教堂了,将来有一天,他的画像可能也要挂上教堂。
那么,当年罗马征服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这帮祭司还是非常的一神论,从而对罗马的政权构成了一个极大的挑战。罗马的政权也是什么呢? 凯撒崇拜。凯撒崇拜之下有宗教自由,你们爱信什么样的神,你们愿意信100个神,我都不管,只要你要加上凯撒崇拜。诸神万神,都在凯撒崇拜之下。
所以,罗马建立了一个万神庙。凡他征服的地方,这个地方的神就会拿到万神庙去。万神庙就是今天属灵的中国政协,各个地方的三教五流、七老八贤的全部都进来,成为政协委员。所以到二世纪初的时候,罗马的万神庙里的神,有人统计说,真的超过了一万个。当时有种说法——罗马城里,平均每个罗马公民都能分到一点几个神。
所以,在这个万神的多神的世界之上,罗马是以凯撒崇拜来统领一切。只要你承认凯撒崇拜,你们自己的宗教我们就不管。罗马在任何地方都是这么做的,这种做法在任何地方都行得通,只有到了耶路撒冷行不通。罗马帝国说,我们允许你,你的这些自由都可以,但是,我们要把“五圣写真”——只是现在活着的那个凯撒的写真——挂到你的圣殿里去。结果,这种做法就遭到了公会的殊死抵抗。
这样的事情,在本丢.彼拉多上台之前,前面好几个总督和他们发生了很多次。曾经有一次最剧烈的,就是一帮祭司站在圣殿的门口,堵在那里不走,不让你能够把那个凯撒的像挂进去,因为那是亵渎一神的。罗马的总督就命令士兵用标枪一个一个地把他们刺死。但是,后来仍有太多次猛烈的反抗,到本丢.彼拉多的时候已经很温和了:我们给你们划一块圣殿区域,你们自己建立卫队负责治安,我们不管,我们的人也不进去。凡是罗马人,罗马军队,如果越过那条线,就是违法。这是非常优待你们了。这是一个宗教特区了。
所以罗马人,有的时候也很委屈,你得理解他的用心啊,因为他如果不信神的话,他会觉得很委屈:我们已经很宽容了,我们在帝国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像这里一样对你们这么好,你还要我们怎么样?有的时候,我们和共产党一些干部打交道,他们也是这样的:我们已经够宽容了呀,你还想怎么样?在他们的理解里面,已经不错了!悠着点,已经可以啦,你还要怎么样!
一神的崇拜就是要打破这个政主教随的帝王和国家的崇拜。这个打破,不是说我们上街去打破,不是说我们用那个或这个去打破,而是通过福音的传扬和十字架的道路,通过教会的受苦,慢慢地——当然上帝也掌管整个普遍历史——慢慢地去打破。
这里碑文的马屁拍得很厉害:“龙髯虽逺”,其实这人都已经死了嘛。“弓剑可攀”,就是丰功伟绩还永远地留在我们心中。“日角舒光,天颜咫尺”,那不是在讲耶稣,不是在讲他虽然离得很远,但是实际很近;他这里讲的是,皇帝是“以马内利”的皇帝啊!“天颜咫尺”,那就是把“以马内利”给挂进来了。
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实际上1400年来,基督教未曾对中国文化构成真正的挑战,就是因为他一直降伏在,或者自愿地妥协在帝王崇拜之下,成为三自教会、成为爱国教会,一直和其他外来宗教一样,伏在基督教中国化的道路下面。
那么,唯有最近60多年来的家庭教会,我们不挂靠、我们不登记、我们不挂“五圣”的像,我们愿意为此承受逼迫、屈辱和藐视,活在这个社会的边缘地位。这个,是我们所信的福音;这个,也是我们信福音的方式。
阿罗本在公元641年的时候,其实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但是,这个文献因为后来唐武宗灭佛,(景教受牵连)就一直躺在敦煌这个地方,因此没有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他写的就叫《一神论》,可惜这个一神的观念,在1400年的基督教在华史中,没有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也没有知识分子读到这个东西。
你看,文献的第一段非常清楚——“万物见一神”。这句话好有气魄!“万物见一神,一切万物,既是一神,一切所作若见;所作若见,所作之物,亦共见一神不别。”这个就叫“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他用到了罗马书一章二十节的一句经文。 “以此故知一切万物,并是一神所作。可见者不可见者,并是一神所造。”这就是《尼西亚信经》所讲的“创造天地和有形无形万物的主”。“之时当今,现见一神所造之物,故能安天立地,至今不变。”这个是景教一神论的核心,尽管还没有到基督教救赎的那个核心,可是,如果这个一神的观念在中国强有力地进来,那么,将在帝王崇拜之间构成非此即彼的争战。
可是,这个争战1400年来并没有发生,而只是一个漫长预备。直到马礼逊来华,直到宗教改革的信仰来华,直到二十世纪,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成。以人为神,以帝王为神,以权力为神,这三大崇拜仍然没有改变。当然,从传统社会来讲,我们说的政治层面的帝王崇拜,文化层面的孔子儒教的崇拜,私人层面的祖先崇拜,这三个东西在今天的中国社会,后面两个虽然已经慢慢地在消退,但是,还是有非常强大的民间文化的基础,仍然存在着一些文化层面的变形。尽管如此,在国家层面的那个崇拜,完全没有被改变过。
五、新教对今天中国文化的三个根本挑战
所以,让我这样来总结今天新教对中国文化的三个最根本的挑战。
1、一神论对偶像崇拜的挑战
第一,是超自然的独一神论,对国家主义的一党独裁这一本质上的偶像崇拜,在国家政体的意识形态层面的挑战。这一个挑战没有完成。这一个挑战很大程度上很难通过卑微的弱小的教会来完成,乃是由上帝在历史中的反复地击打而进行的。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神的手在这种崇拜上面,反复地击打这个国家,反复地击打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反复地击打这个国家的政权,反复地击打这个国家的命运,直到今天。
从这样的角度来讲,我们一个方面要更多地与中国所经历到的每一次的苦难感同身受,与中国人一同地承受这个中国历史中的苦难,但是在另一个方面,我们的确知道我们的悖逆,除非神在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地击打,否则,超自然的独一神论无法摧毁这一个本质上的偶像崇拜!
2、救赎论对自我称义的挑战
第二,是唯独恩典的救赎论对道德至上的儒家传统和实用主义的世俗生活的挑战。中国整个的文化在生活和伦理的层面,本质上是一个行为主义和律法主义的称义系统。一是帝王崇拜的崇拜系统,二是道德行为的称义系统。在这个称义的系统中,以人的道德的成就和行为,包括这个行为的可测量来称义;到了民间社会,就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行为主义来自我称义,而不明白、不知道什么叫恩典。
中国80年代的新儒家学者里面,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学者,后来信了主,就是郑家栋。大概在一年前,我在一次讲座中特别地引用了郑家栋老师的一些看法。郑家栋在80到90年代,是中国最早兴起的一批新儒家学者中的一位,但是,后来他为什么信主了呢?他在个人私德上面出了很大的丑闻,但是,我们关心的不在这里,因为这是公共的事件。
对于儒家传统,为什么我们说一个方面这是道德的称义?为什么鲁迅说翻开2000年的礼教的历史,只看见了一个词——“吃人”?就好像我们今天讲的,神所赐的律法本身是圣洁的、纯全的,可是,律法本身并没有为你提供当你不能够遵循这律法的时候,救赎之道和出路在哪里。这律法本身不能够拯救人。所以,中国的道德文化的实质是说,你可以讲得很漂亮,你可以提出很好的东西,可是,你没有办法解决一切的事情——就是当人做不到的时候,就没有出路。当人做不到,也没有人做得到的时候,在中国的儒家文化中,他们一定是死路一条。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一个女性如果失贞,她的结局是什么?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下面,她有没有出路?她没有任何出路!甚至很多的时候,不是她自己犯罪,有可能是被强奸。就算她是被强奸,就算她完全是一个受害者,在2000年的中国儒家文化中,有没有出路?没有任何出路!
这就是儒家文化最可悲和最可怕的地方。不是说它的道德理想不对,但是,它带来了一个称义的系统,那个称义系统一方面带来了那些以此称义的人的狂傲自大,另一个方面又带来了对于芸芸众生的一种道德的统治、一种道德的捆绑、一种道德的绑架,一直到最后——完全没有出路。
所以,郑家栋也一样,作为一个儒家的学者,他自己在私德上出了问题,他就在整个的中国知识界混不下去了。你明白这一点吗?他没有翻身的可能。他无论怎么懊悔,他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在中国文化中,做一个中国人是绝对不可以失足的。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绝对不可以失足,一失足就成千古恨,永远没有翻身的出路。
这就是道德文化的可怕!为什么?因为没有恩典、因为没有救赎,不可能再被接受了。所以,郑家栋在儒家圈子里混不下去了,没有人能够接受他。只有耶稣能接受他,只有在基督那里,给一切的穷乏者、给一切的失足者、给一切的受害者、给一切在道德面前的失败者,提供了恩典和出路!
在教会的历史上,你可以看到,奴隶起来成了教宗,杀人犯起来成了牧师。哇,这样子的事情太多了!在中国的文化中,这是绝对不可能想象的事情。没有恩典的闯入,这个道德自义的文化,是没有办法翻转的。
所以,很多人说,为什么在中国没有忏悔?为什么在中国的文化中,为什么经过了文革,仍然看不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忏悔?为什么在中国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在中国,忏悔就死定了!在中国的文化中,就算别人知道了,你都不要说——不承认,就不承认,打死都不承认!这样,你才混得下去。忏悔的结局,就是你死定了,就是你彻底出局。
3、教会论对集权社会的挑战
第三,是教会观——圣约社群论,对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社会的挑战。基于血源的宗法社会,是中国的传统社会,那么,今天中国传统的宗法社会没了,而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社会,其实这是一盘散沙的“流民社会”,按社会学家费孝通的说法,应该是“有国家而无社会”。
中国的传统是有国家而无社会。当然也有一些“社”。社这个词,鲁迅的短篇小说《社戏》,就是写中国传统的那个民间庙会,但是,它不是一种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公民社会。中国的传统社会,除了宗法社会——就是基于你的家族体系之外,在国家和个人之间,是没有民间社会的,是没有公民之间的自由结社的。不论或男或女,无论是山东人还是广东人,山东人都去山东商会,广东人就去广东商会。没有四川人和山西人都在一起的,没有自主的人和为奴的人都在一起的。商人就去商会,劳苦大众、卖苦力的,就去码头工人的青帮。大家各去各的,没有一种突破了血缘,不在皇权的统治之下而建立起来的一个自由人的自由的生命共同体。中国文化中没有这个东西。传统社会没有,今天也没有。
今天中国的社会,你想一想,除了家庭教会以外,在中国社会中,哪里可以看得到完全脱离共产党的统治辖制和官方系统之外的自由人的自由结社呢?哪里有?完全没有! 连同城一起聚会,现在要被抓;连微信群主,就要被抓。
第一个层面是在国家崇拜系统的层面,第二个层面是在称义的伦理系统的层面,而第三个层面是在社会结构的层面。在社会结构的层面,从古代一直到今天,从鸦片战争到今天已经140多年了,仍然没有任何的变化。除了官家,就没有其他家,哪怕是做生意。中国今天的私人老板,可以自由结社吗?也是不能的,一样要挂靠才可以的。不挂靠,仍然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没有改变!
所以圣约社群,所以一间一间的教会,在这里面什么人都有。有大学教授,也有上访者,有害过人的,也有被人害过的。以前我们教会很感恩地说,有国民党的后代,有共产党的后代;有当过红卫兵砸过人家的,也有以前被红卫兵砸过的;有老板也有雇员。哇,他们在一起,他们在主里跨越了社会血缘、宗法,还有权力、知识这一切的社会分层。只有教会在中国社会,能够带来这样的一个跨越一切社会文化分层的真正的社会。
1842年鸦片战争之后,只有五口通商,宣教士只能去这五个地方。在19世纪后半叶,到了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天津条约》,到了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国就开始把整个内地向宣教士和西方人开放,让他们可以在内地任何的城市,可以置买房产,开始宣教护道。
所以,从1860年到1900年的义和团中间的40年中,教案不断。那个时候的教案,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时候教案的冲突,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主要冲突,不是在第一个层面与清政府的冲突。在清政府那里,因为打了败仗,所以还是比较宽容的政策,不想搞事。而且地方官员呢,如果出了这种教案,通常情况下还是会把这帮刁民拿来骂一顿,息事宁人。那么,到1900年就不一样了,官方和民间全部合立起来了。
在那40年中,主要的教案都是这样爆发的。乡绅是反教的主力。什么是乡绅?就是读过书,但是没有考中进士的。在中国文化中,书读得一般、中等成绩的人,应该就是构成中国民间社会的主力。这个就叫乡绅。所以,乡绅一般都是当地有文化、有道德、有体面、有声望的这样的人群。为什么乡绅是反教的主力呢?乡绅出来反教,民间的老百姓一呼百应;然后发生问题之后,上级的官员把他们压下来。基本上是这个模式,一直到1900年,上面就不压了,上面就开始鼓动了,然后,上下一起反教了。
为什么乡绅是那40 年中的主力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这个层面。你想一想,在一个传统的村子里,是乡绅统治的,官员也是不进来的,背后是宗法社会,是血缘社会。那么,现在有人信主了,来了一个宣教士,整个乡村里的社会结构都被改变了。还有整个民间的宗教,那个时候有迎神赛会、庙会。秋收了,整个村都要有各种民间的宗教仪式。
按传统,家家户户都是要摊派费用的。家家户户都要摊派,就是这家信耶稣的,他说我信了耶稣,我不参加这个活动。这个冲突就很大啊——你敢不出钱啊?而且民间的精神领袖也在发生变化。原来去祠堂,现在去教堂。祠堂旁边多了一个教堂,是对整个社会结构的冲击。
所以,在那40年中,冲突还没有到达国家的这个层面。在社会结构的层面,最强烈反教的是士绅阶层,直到今天也是一样的。新教对中国文化的三个根本的挑战,第一是神论,就是超自然的独一神论。第二是救恩论,唯独恩典的救赎论。第三是教会论,圣约社群的教会论。这三个挑战,冲击了中国文化中最核心的地方,直到今天也是这样子。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结语:求主扭转、更新和掌管中国文化
我差不多就讲到这里。我本来想反过来再讲一个,只好放到以后了,就是中国文化反过来对基督新教的挑战,也包括我对宣教本身的一些反思。列文森——他与费正清都是美国汉学界最重要的人物——在他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这本名著中,很仔细地分析了基督教为何在中国失败。这本书写在50-60年代,他看到了1949年共产党的得胜,看到了50年代的三自运动,然后一直看到66年的文革,所以,在他那里看到的是——基督教在中国已经彻底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机会看到80年代的时候,突然冒出来几百万的基督徒和大量的教会。所以,他在书中分析说,140年的宣教史,为什么带来中国文化的抵挡?为什么带来中国文化中那么强烈的反教的精神?为什么到49年、到50年代和60年代带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彻底失败?他不信主,不过,他有很多的观察。这个是反过来的挑战。
我这个讲座的题目叫做《宗教改革与中国文化的挑战》,其实这是有点歧义的。事先是想讲两个方面:一个是宗教改革、新教入华对中国文化本身的挑战,就是我刚才讲的。另一个是中国文化本身对于这个宣教本身的挑战,对于这个现代的基督教本身的挑战。因为这是一块硬骨头,硬骨头就挑战你牙口好不好?今天没有时间讲了,就停在这个地方。
我想用两段经文来结束。当保罗去传教的时候,我们说保罗是以卑微的方式,用弱势文化进到强势文化中。我想请你们和我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第2-4节)阿们。
我们愿,这也是我们的心志——我在中国的文化中,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在这样的处境下面,我们真的是又软弱,又惧怕,又战兢。但是我们讲神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也不妥协那智慧委婉的言语,而是依靠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的教导:“ 没有人把新布补在旧衣服上;因为所补上的反带坏了那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惟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第16-17节)阿们。
我们求主在中国继续做那个奇妙的工作,就是将新酒装在新皮袋里。这个不是我们能做的,这是上帝掌管整个中国的历史而做的。而这个新皮袋不是说,要把中国文化和社会都否定掉,而是当一个文化的核心被扭转的时候,当那一个敬拜系统、称义系统和社会结构三个方面的中国文化最核心的东西被扭转之后,中国文化在下面的低一点的层面里,上帝的普遍恩惠才会被更新。
那个时候我们也一样地说,唐诗宋词真的也很美,我们在文化上也是享受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汉语中的那种中国人文化的意义。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与“多一个中国人少一个基督徒,还是多一个基督徒少一个中国人”这样的新酒与旧皮袋的冲突,唯有在神的那里,他能够更新,他能够掌管。我们在神的面前向他祈求。阿门。
我们现在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恩典临到我们。主啊,独一的神临到这一个偶像林立的国家和民族。主啊,那一个甚至超越的、将来的、永生的盼望,临到这一个实用主义的、以今生为重的伦理社会的文化。主啊,那一个帝王的崇拜,那一个集权的专制,仍然辖制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灵魂。主啊,我们求你可怜我们。主啊,我们求你再一次将你的怜悯和恩典临到我们,不单是在这个体制下面的老百姓,而且也是在这个体制中的每一个人,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一样地被这权力辖制到可怜的地步,被帝王的崇拜、权力的崇拜辖制到可怜的地步!
主啊,求你怜悯我们。求你用你的大力打碎,主啊,你继续地打碎。主啊,你在过去100多年中国历史上所做的,求你继续地做下去,求你使我们仰望、忍耐、等待你大能的作为,而愿意以受苦的、卑微的、耐心的方式来等待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求你因此来激励我们当中,无论是传道人,无论是代职的同工,无论是每一位基督徒,主啊,我求你在今生来使用我们,让我们的心为你的国度而跳动,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是为你的名奔跑!让我们痛恨我们自己里面的老我,痛恨那一个罪人的中国文化在我们里面的那些各样的残留,求主你打碎那里面的一切的偶像,求主你来除掉那里面的一切罪孽,求你来拆毁那里面的一切隔断的墙!感谢赞美神,听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